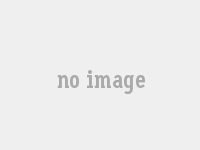來源
宋神宗在熙甯年間(1068——1077)重用王安石變法,變法失利後,又在元豐年間(1078——1085)從事改制。就在變法到改制的轉折關頭,發生了蘇轼烏台詩案。這案件先由監察禦史告發,後在禦史台獄受審。禦史台自漢代以來即别稱“烏台”,所以此案稱為“烏台詩案”。
發生時間
“烏台詩案”是元豐二年發生的文字獄,禦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蘇轼《湖州謝上表》中語句和此前所作詩句,以謗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蘇轼,蘇轼的詩歌确實有些譏刺時政,包括變法過程中的問題。
起因
總的來說可以歸結為政治上為政敵所不容,文字上又授人以把柄。蘇東坡,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過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台,吐之乃已”。
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蘇轼轉知湖州。詩案就是蘇轼到湖州任所時寫的《湖州謝上表》引起的。表中說:“臣……荷先帝之誤恩,擢至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陛下……知其愚不識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蘇轼這幾句牢騷話,筆下的“新進”,指的是王安石變法時被引進的一批投機鑽營的“群小”。“生事”一詞,已成為保守派攻擊變法派的時下習慣用語。這些用語自然刺痛那些仍然竊據高位,謀取私利的“小人”。
第一個站出來檢舉蘇轼的是禦史裡行何正臣,緊接着是王安石的學生李定。宋神宗在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的百般構陷下,隻得降旨将蘇轼交禦史台,由李定為首的“根勘所”負責審理。他的筆觸更加尖刻犀利且指責積貧積弱的朝廷,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得到平複,然而,“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東坡行雲流水之作引發了烏台詩案。這樣,一個駭人聽聞的文字獄便揭開了序幕。
結果
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李定等人奉旨查辦,立即派太常博士皇甫遵才前往湖州逮捕蘇轼。八月十八日,蘇轼被解到京城,投入禦史台獄。兩個多月的“根勘”審理,蘇轼受盡非人的折磨。禦史台嚴刑拷打,晝夜逼供,真是“诟辱通宵不忍聞”。最後,李定等人強加給蘇轼“四大罪狀”,請求宋神宗處死蘇轼。
宋神宗面對禦史台的奏報,心裡也着實犯難。當年宋太祖趙匡胤曾有遺囑:除了犯叛逆謀反罪,一概不殺大臣。李定等人必欲置蘇轼于死地,朝野上下,輿論嘩然,認為蘇轼未犯叛逆罪,不該重處。更奇怪的是,新舊兩派正直之士,均出面營救。由于各方面的營救和輿論壓力,促使宋神宗産生寬貸蘇轼,從輕發落的念頭。最終,蘇轼得輕判,以“蒙恩責授黃州團練副使”結案。
背後
當蘇轼步入仕途,剛開始就被任命為福昌縣的主簿,(就是現在的河南伊川縣)。這隻是一個幫助知縣處理文書檔案的九品小官。蘇轼的知名度在此時已是很高了,他的文章确實寫得很好,得到了宰相韓琦和知制诰王安石的器重。很快就升遷到陝西鳳翔、杭州等府任通判。直到宋熙甯七年(公元1074年)升任密州(山東諸城)太守,後又改任徐州、湖州太守。當時官員赴新任都要向皇帝上謝表,所以蘇轼照例向皇帝呈遞《湖州謝表》,由此惹下了一生的禍端。
第一
蘇轼反對王安石變法此時,新法的領袖人物王安石和呂惠卿都相繼下台,但禦史台仍然為新黨把持。
第二
他們對蘇轼的才華和很高的名氣心懷忌恨。在《湖州謝表》裡,他寫了這樣幾句話:“知其愚不适時,難已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是在向皇帝說:“您知道我愚笨跟不上時代,怕我與那些新進人物搞不好關系。但知道我老實本分,也許在外州郡治理百姓還可以。”這自然是有意攻擊那些推行新法的政客。
禦史中丞李定對宋神宗說:“蘇轼說因為他不生事,才把他放到外郡任職。難道我們這些留在朝中的都是愛生事的?這不是明目張膽地在攻擊皇上施行新政為‘生事’嗎?”他還指出蘇轼的四條罪狀:1始終堅持自己的錯誤,毫不悔改;2他的錯誤言行流傳很廣影響很壞;3他很會強詞奪理、蒙騙人們;4對陛下不使用提拔他心懷怨恨。象這樣的人不加嚴懲,要國法何用呢?
于是便對他近年來寫的一些詩詞,加以曲解、牽強附會羅列罪名。
受害人
烏台詩案受牽連的共七十多人,其中有二十九位大臣和名士受到不同處分。王诜、蘇澈等受貶斥,張方平、司馬光等僅因收藏蘇轼諷刺文字未申繳入司,各被罰銅二十斤。
對蘇轼的影響
夢後的黃州貶谪生活,使他“諷刺的苛酷,筆鋒的尖銳,以及緊張與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現的,則是一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的識諧.醇甜而成熟,透徹而深入。”在下棋時,他體悟到:“着時自有輸赢,着了并無一物”。在幽林靜山之間,他豁然開朗:“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耐客思家”。他不再執著于“奮力有當時志世”而是“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所以當蘇轼遨遊赤壁之時,面對“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發出“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的感歎,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飄然獨立,隻願做一隻孤鴻:“揀盡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在文化上
前期尚儒而後期尚道尚佛。
前期
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獲得成功,即使有“歸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會責任,他深切關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饑”;他渴望在沙場上一展雄威,“鬓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時,其銳意進取、濟世報國的入世精神始終十分強勁。蘇轼在其政論文章中就曾一再闡發《易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能動于改革,為變法搖旗呐喊。
後期
尤其是兩次遭貶之後,他則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歸到佛教中來,企圖在宗教上得到解脫。他認識到自己和朝廷權貴們已經是“肝膽非一家”。所謂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對他來說已經是“鶴骨霜髯心已灰”,隻能勞神費力,再沒有什麼“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壯志,“窮猿已投林,疲馬初解鞍”。對那個一生仕宦起伏颠簸的蘇東坡而言,他從心底發出最最真實的慨歎“惆怅東南一隻雪,人生看得幾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啟發,在黃州惠州儋州等地過上了真正的農人的生活,并樂在其中。
當太後允其在太湖邊居住的時候,他大喜:“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為田舍翁。”他終于可以乘一扁舟來往,“神遊八極萬緣虛”了。久旱逢甘露,蘇東坡和農人完全一樣快活而滿足,他寫詩道:“沛然揚揚三尺雨,造化無心恍難測。老夫作罷得甘寝,卧聽牆東人響屐。腐儒奮粝支百年.力耕不受衆目憐。會當作溏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知我囊無錢。”
在風格上
前期的作品大氣磅礴、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一瀉千裡;而後期的作品則空靈隽永、樸質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遠溢清。就詞作而言,縱觀蘇轼的三百餘首詞作,真正屬于豪放風格的作品卻為數不多,據朱靖華先生的統計類似的作品占蘇轼全部詞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個時期創作的主流。n
有詞如“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緻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遊卒歲,且鬥尊前”鋒芒畢露;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獵》決不可“十七、八女子,執紅牙闆”來悠然而唱,而必須要“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這些作品雖然在數量上并不占優勢,卻着實反映了那段時期蘇轼積極仕進的心态。n
而後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風貌,也有娛賓遣興,秀麗妩媚的姿采。諸如詠物言情、記遊寫景、懷古感舊、酬贈留别,田園風光、談禅說理,幾乎無所不包,絢爛多姿。而這一部分占了蘇轼全詞的十之八九左右。雖然也有“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的大悲歎,但更多的卻是“花謝酒闌春到也,離離,一點微酸已著枝”的小恻隐,他逃離了仕途官場的蠅營狗苟,開始靜觀自然:“林斷山明竹隐牆,亂蟬衰草小池塘”;他越來越覺得文字難以承載内心之痛:“斂盡春山羞不語,人前深意難輕訴”。n
他将自然與人化而為一:“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其間大有莊子化蝶、無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對現實的對政治的不滿、歇斯底裡的狂吼、針尖麥芒的批判全部驅逐了。其題材漸廣,其風格漸趨平淡緻遠。
後人評價
蘇東坡到黃州來之前正陷于一個被文學史家稱為“烏台詩獄”的案件中,之後,他從監獄裡走來,被人押着,遠離自己的家眷,沒有資格選擇黃州之外的任何一個地方,朝着這個當時還很荒涼的小鎮走來。他不知道,此時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載史冊的文化突圍,他寫于黃州的那些傑作,既宣告着黃州進入了一個新的美學等級,也宣告着蘇東坡進入了一個新的人生階段。n
我非常喜歡讀林語堂先生的《蘇東坡傳》,但每次總覺得語堂先生把蘇東坡在黃州的境遇和心态寫得太理想了。語堂先生酷愛蘇東坡的黃州詩文,因此由詩文渲染開去,由酷愛渲染開去,渲染得通體風雅、聖潔。其實,就我所知,蘇東坡在黃州還是很凄苦的,優美的詩文,是對凄苦的掙紮和超越。-----餘秋雨的《蘇東坡突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