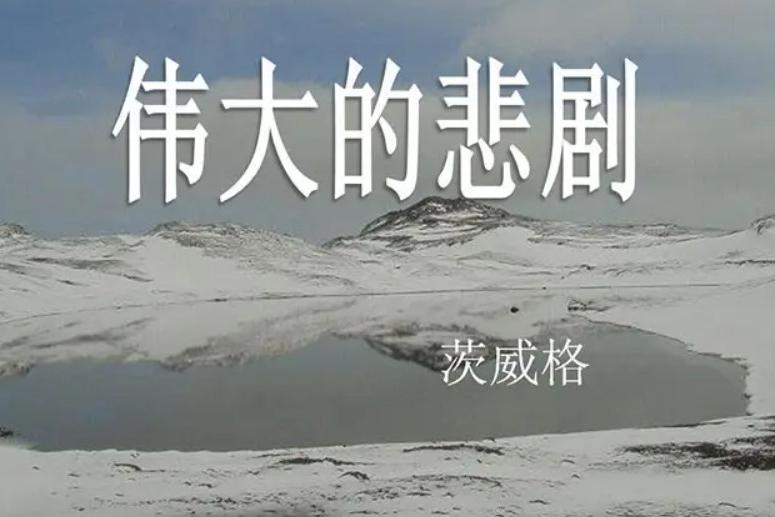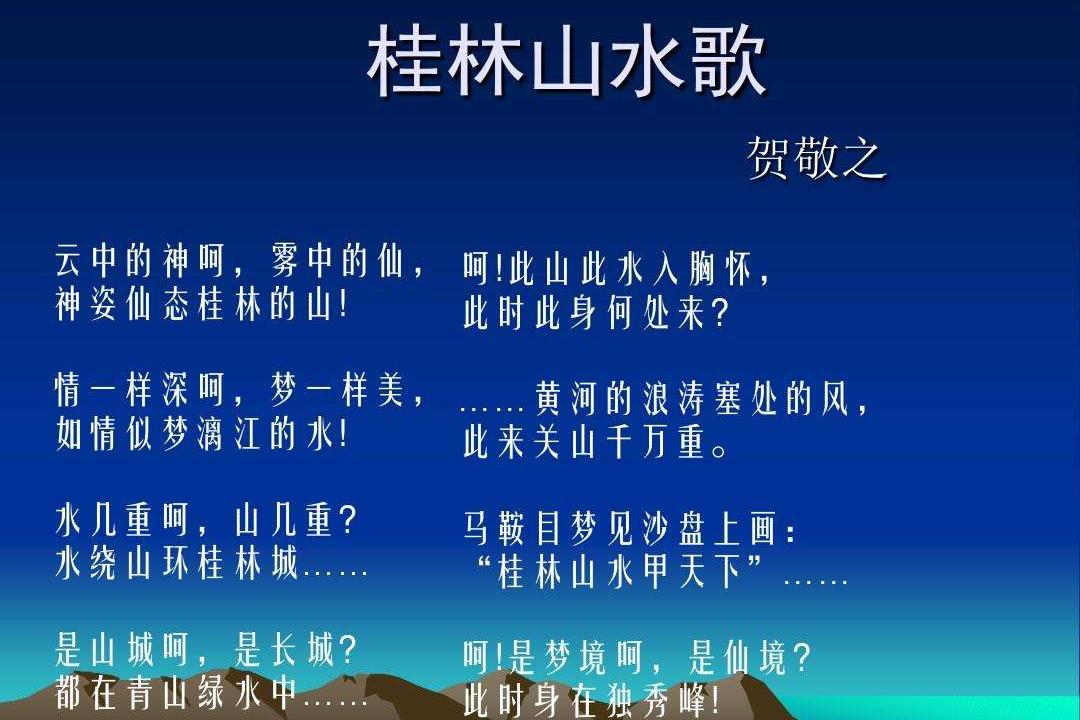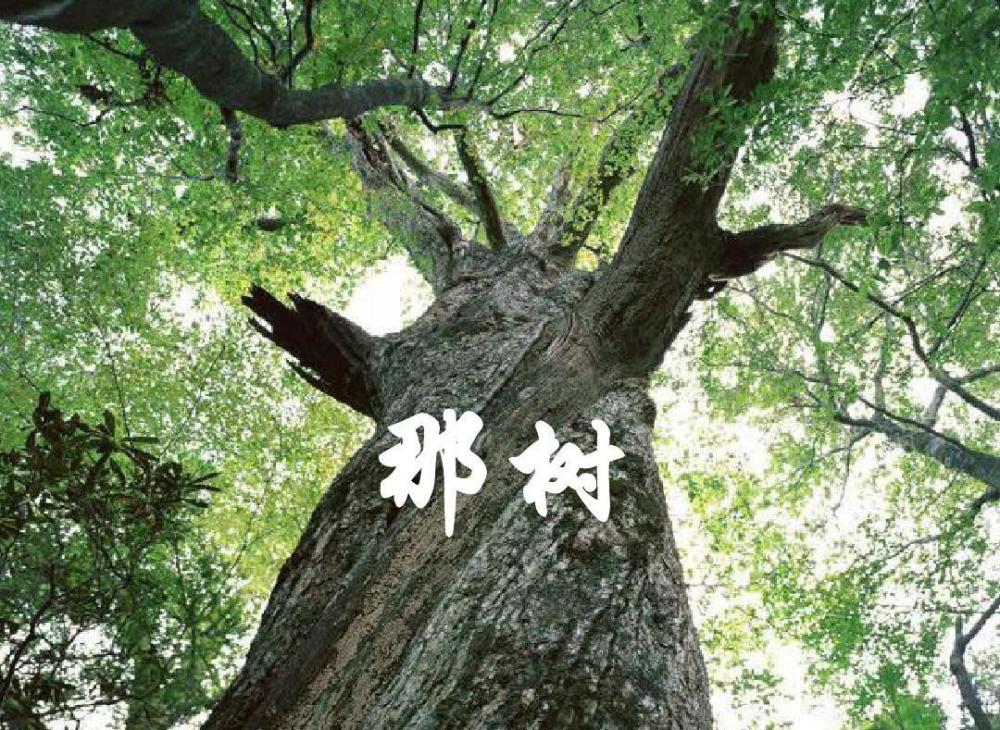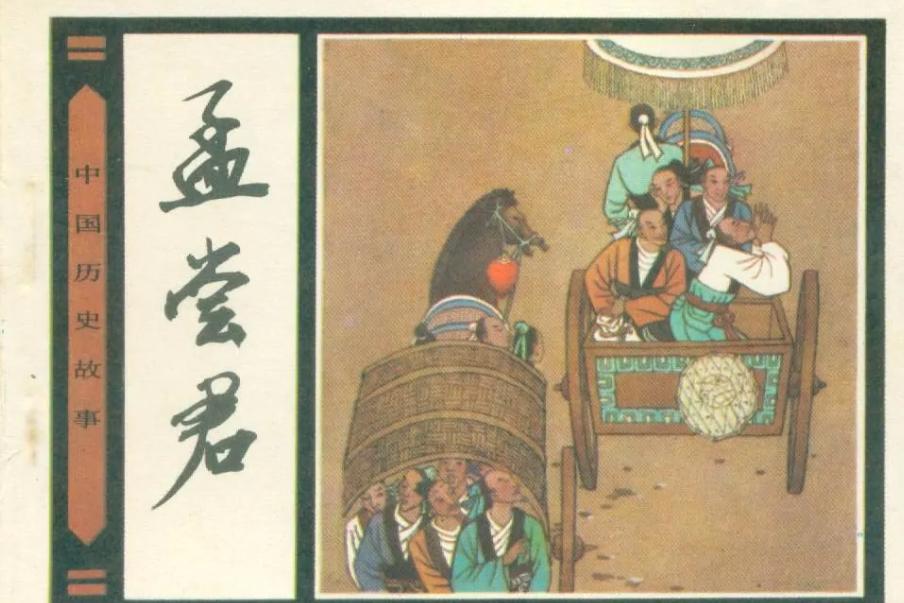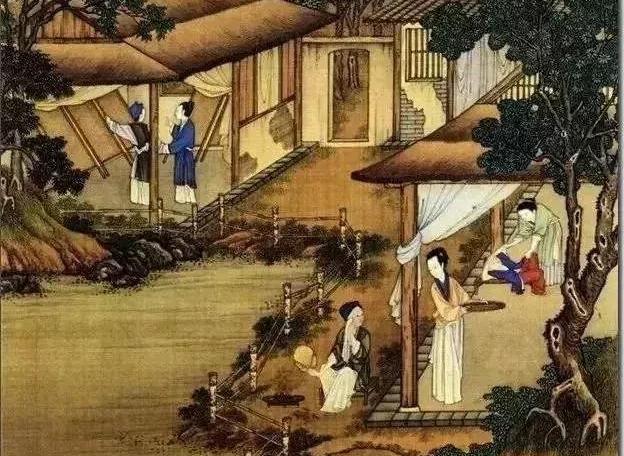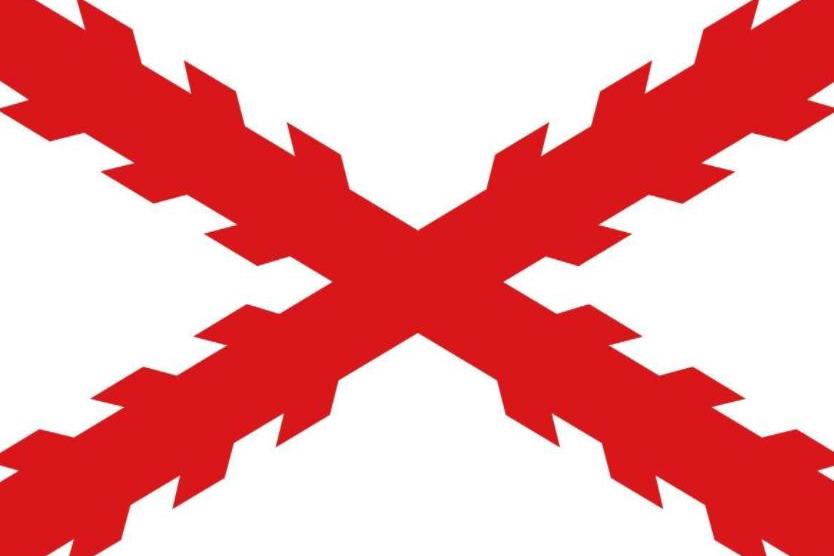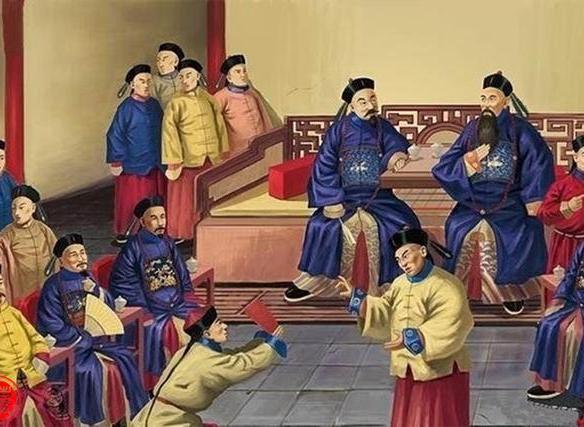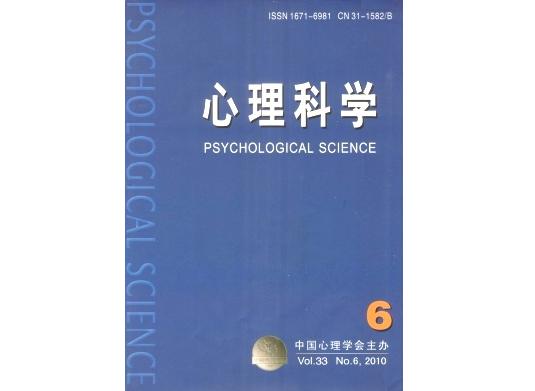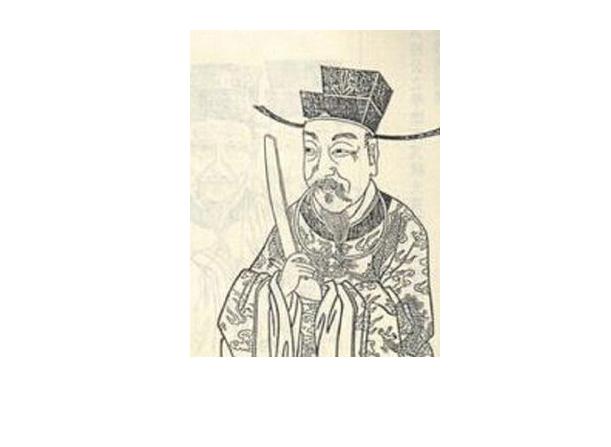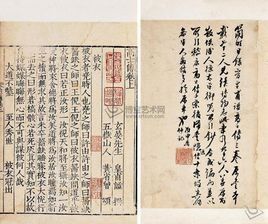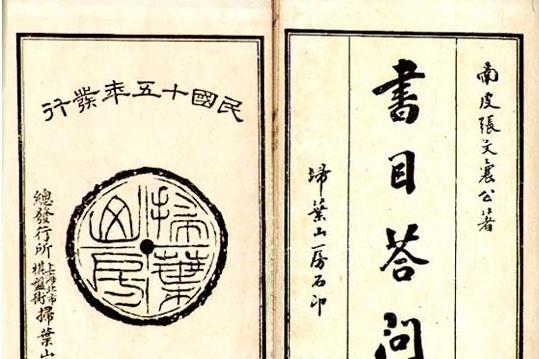内容簡介
1912年1月18日,斯科特一行繼挪威人阿蒙森之後登上了南極極點。返回的途中,他們拖着羸弱的身子,蹒跚行進在皚皚白雪上,經過70多天的死命掙紮,當燃油與食物均已告罄時,終于被南極寒冷的暴風雪吞噬,長眠在茫茫冰雪當中,演繹了一場人類探險史上的悲劇。
創作背景
1910年6月1日,斯科特帶領探險隊離開英國,前往南極。1911年10月,他們在新西蘭的埃文斯角附近登陸,準備在當年12月至次年1月左右征服南極點。可就在這個時候,他們得到消息,挪威人阿蒙森率領另外一支探險隊正向南極進發,要“和他争奪第一個揭開冥頑的地球的秘密的榮譽”。于是,斯科特一行于11月1日匆忙出發,“去争取國家的榮譽”。經過一番激烈的競争,結果是阿蒙森隊捷足先登,于1911年12月14日到達南極,而1912年1月18日,斯科特隊才到達,比阿蒙森隊晚了将近五個星期。最後,阿蒙森勝利而歸,成功的旗幟永遠飄揚在南極點上,而斯科特等五名沖擊南極的英雄,因為南極寒冷天氣的突然提前到來,饑寒交迫,體力不支,在返回的路上與嚴寒搏鬥了兩個多月,最後長眠在茫茫的冰雪之中。《偉大的悲劇》就是斯蒂芬·茨威格于1927年依據斯科特探險隊遺研下來的一些底片、電影膠卷、日記遺書等創作的,目的是為了紀念人類曆史上最早到達南極點的兩名科學探險家——挪威人阿蒙森和英國人斯科特。
人物介紹
斯科特帶領的科考隊的五人
羅伯特·福爾肯·斯科特:英國海軍上校,他是一個堅強、高尚的人,帶領其他四人到達了南極點,最後卻因暴風雪不幸悲慘地去世。
埃德加·埃文斯:英國海軍軍士,本來是一個強壯的人,卻因精神失常,嘴裡總是念念有詞,最終不幸去世。
勞倫斯·奧茨:英國皇家禁衛軍騎兵上尉,最後因病而離開了斯科特一行人,向死神走去。
愛德華·威爾遜:斯科特的夥伴,是個堅強的人,克服了許多困難,可是最後因被大自然戰勝,像親兄弟似的摟着斯科特迎接死亡。
亨利·鮑爾斯:斯科特的夥伴,率先發現了阿蒙森的捷足先登。
作品鑒賞
主題思想
《偉大的悲劇》的主題思想是:真正的英雄身上,永遠閃爍着崇高的精神光芒,探險隊員們的美好品質主要有:
其一,與死亡抗争、為科學獻身的英雄氣概。五位勇士選擇了探險,同時也就選擇了犧牲,有着為祖國而獻出一切的崇高的精神境界。他們戰勝嚴寒,艱難跋涉,一路與自然、與生命抗争,終于到達了南極,卻居于挪威人之後。看到“挪威國旗都在耀武揚成、洋洋得意地在這被人類沖破的堡壘上咧咧作響”,這是痛苦心理的真實寫照,但他們還是用理智、誠信戰勝了自己,犧牲自己的事業。兩位戰友離他們而去,他們也明白了“希望都破滅了”,面對死神的到來,他們做了最好的選擇,威爾遜在雪橇上還裝上了礦石。為了事業,可以犧牲自己,斯科特他們在糧食、燃料皆盡的情況下,不是懦弱、恐懼,“沒有哀歎過一聲自己最後遭遇到的種種苦難”,而是“驕傲地在帳篷裡等待死神的來臨”,從容地選擇犧牲。
更可貴的是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斯科特上校用僵硬的手指一直記日記,寫給所有的親人,“在白雪皚皚的荒漠上,隻有心中的海市蜃樓”,直到筆從僵硬的手中滑下來為止。這需要一種多麼超人的勇氣和毅力。一個勇敢的探險隊員,為了祖國和人民獻出自己的生命,在其筆端流露出對祖國、對親人、對朋友的思念之情,沒有豪言壯語,沒有悲痛哀傷。作者把這一場面描述得非常細膩,真實地再現了斯科特普通而又高尚的内心世界,給人以極大的感染,引起感情的共鳴。
其二、互幫互助、團結協作的集體主義精神。五位勇士是一個團結合作的集體,是一個兄弟般的集體,在艱難的環境中鑄就的牢不可破的集體。在歸途中,五個勇敢的人面對寒冷、冰凍、飛雪、風暴,他們的腳早已凍爛,禦寒物品已殘缺,燃料也成問題,更可悲的是食物也越來越少,身體也越來越弱。但五個人還是互相幫助、互相鼓勵着艱難地前進,誰也不願把誰落下,誰也不忍讓誰先離集體而去。不幸的事還是發生了,戰友埃文斯突然精神失常,他站在一邊不走了,嘴裡念念有詞,不停地抱怨着他們所受的種種苦難,有的是真的,有的是他的幻覺,面對瘋了的戰友,在斯科特的日記裡,找不到抛棄他的理由,隻有患難相伴與戰友的友誼。在1912年2月17日的一個夜裡,這位英國海軍軍士離他們而去,在人類的史冊上譜寫了一曲生命的友誼之歌。作者飽含感情地描寫了斯科特,當營地的戰友發現他們的屍體時,斯科特還像親兄弟似的摟着威爾遜。五個勇士在生命最後一刻,體現出人世間最珍貴的友誼,戰友的情誼讓他們成為一座不朽的豐碑,真正體現了人生的價值,突出了悲劇的偉大之處。
其三,誠信,勇于承認失敗的紳士風度。當斯科特一行到達目的地時,斯科特發觀雪地有滑雪杆,有人比他們先到達南極,接着他們又發現了挪威國旗時,心中的沮喪和痛苦是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的。“第一個到達者擁有一切,第二個到達者什麼也不是”。美好的夢想成為泡影。“淚水從他們的眼睛裡奪眶而出,他們像被判了刑似的失去希望”。這裡罕無人煙,斯科特他們完全可以拔掉挪威國旗,豎起英國國旗,這樣做還是可以作為第一位到達南極的人,回國後也可以宣傳宣傳,可是斯科特他們沒有這樣做,他們受英國傳統文化的熏陶,主張誠實守信,他們不僅守信,而且還要為第一名挪威阿蒙森他們送信給挪威的哈康國王,斯科特要忠實地去履行這一最冷酷的無情的職責,在世界面前為另一個人完成的業績作證,而這一事業正是他自己所熱愛追求的。這是高尚而又偉大的人格體現,面對成功和失敗,盡管有悲哀和沮喪,但他們還是誠實守信去做了應該做的事。作者一面不遺餘力地展示這些美好心靈,它不是悲慘,而是悲壯;不是憐憫,而是崇敬;不是恐懼,而是無畏。
藝術特色
《偉大的悲劇》文本采用第三人稱内聚焦的方式,如“他們已經驚慌到了極點。在日記中,人們可以察覺出斯科特隊員們是如何盡量掩飾着自己内心中的恐懼,但從強行的鎮靜中還是一再地迸發出絕望的厲叫:“上帝保佑呀!我們再也忍受不了這樣的勞累了”,再或者“我們的戲将要悲慘地結束了。”
最後,終于出現了可怕的自白:“隻願上帝能夠保佑我們吧!我們已經很難期盼人的幫助了。”不過,他們還是強拖着疲憊的身軀,絕望地向前繼續走啊,走啊。奧茨越來越走不動了,越來越成為朋友們的一個負擔了。在一天中午,氣溫已經達零下40度。不幸的奧茨不僅已經感覺到,而且心中也十分明白,再這樣下去,他可能會給隊友們帶來可怕的厄運。于是奧茨作好了最後的準備。他向隊友威爾遜要了近十片嗎啡,為的是在必要的時候能快速結束自己的生命,不拖隊友們的後腿。
隊友們陪着這個絕望的病人又艱難地走了近一天的路程。但是這個不幸的奧茨卻要求他們将他自己留在睡袋裡面,想要把他們的命運同自己的命運分離開。但隊友們堅決地拒絕了這個主意,盡管他們非常清楚,這樣做無疑會減輕隊裡的負擔。于是奧茨隻好用凍傷的雙腿踉踉跄跄地又走了好一段路程,一直走到夜宿的營地。他和隊友們一起睡到了第二天清晨。清早起來,他們向外面張望,又是狂吼怒号般的暴雪。在這裡,作者以第三人稱内聚焦的視角向讀者展現了幾個探險隊員在面對食物與能源短缺而環境又極端惡劣的情況下的恐慌與絕望的心理活動。
這種視角的運用,充分地敞開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淋漓極緻地展現了人物内心中的起伏與沖突。這種叙述手法的好處是使讀者能充分感受到作品中人物的内心情緒的起伏,從第三個人的視角觀察整個事件的發展,這種内聚焦方式的最大特點是能夠充分地敞開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淋漓盡緻地表現其激烈的内心沖突和漫無邊際的思路。
細節描寫
一、描摹個性的語言。人物語言的細節描寫,可以使人物形象櫥栩如生,使人有“如聞其聲”之感。文本中不幸的奧茨先是要求給他十片嗎啡,以圖盡快結束自己,其他隊員堅決拒絕了他的要求:第二天早晨,奧茨突然站起身來。對朋友們說:“‘我要到外邊去走走,可能要多呆一些時候。”奧茨說到零下40攝氏度外面“多呆一些時候”,這句話意味着勞倫斯·奧茨這個英國皇家禁衛軍的騎兵上尉正像一個英雄似地向死神走去。他給讀者留下的,是笑對死神的勇氣和驚歎。
二、勾勒細小的景物。環境描寫的作用是為了烘托人物形象,而典型環境常常于細小的景物上勾勒出來。文本中對暴風雪的描寫:“刺骨的寒冷吞噬着他們已經疲憊不堪的軀體”、“冰冷的黑夜,周圍是呼嘯不停的暴風雪”、“兇猛的暴風雪像狂人似的襲擊着薄薄的帳篷”、“暴風雪刮得異常兇猛,好像要人的性命似的”等等,這細小的暴風雪之景,渲染了悲壯的氛圍,烘托了英雄犧牲的壯烈。
三、抓住細微的痕迹。事物總是在細微的痕迹上顯出同中有異來。曆盡艱險到達極點,等待斯科特他們的卻是占領者阿蒙留下的國旗和信件,并要斯科特這個失敗者為他完成的業績作證,而“斯科特接受了這項任務,他要忠實地去履行這一最冷酷無情的職責:在世界面前為另一個人完成的業績作證,而這一事業正是他自己所熱烈追求的。文本對國旗和信件的細微描寫,體現出斯科特強烈的愛心、對祖國民族、對事業的一片摯愛之情。
四、攝取細小的動作。一個人不自覺地表現出的細小動作,能反映一個人的個性、習慣和修養。作者描寫了斯科特海軍上校極其冷靜地将日記記錄到他生命的最後一息的情景,描寫了他心中美好的往事及對遙遠祖國、親人和朋友的懷念,尤其是他用已經凍傷的手指哆哆嗦嗦地寫下“請把這本日記送到‘我’的妻子手中!”随後又悲傷地、堅決地劃去了“‘我的妻子“這幾個字,在它們上面補寫了可怕的“‘我’的遺孀”,體現他直面死亡,于細微處見精神,呈現出斯科特他們堅定、執着、勇于為事業獻身的硬漢形象。
作品評價
中國作家段崇軒:《偉大的悲劇》故事發展脈絡清晰,重要情節十分突出。作者舍棄了許多外在的材料,把他的筆觸始終定格在人物的内在層面上去展開,借鑒小說的叙事方式和叙事語言,不僅成功地塑造了斯科特等的英雄形象,而且強烈地表現了作家主體的豐富感情、深刻思想和高尚人格。而作家的這種人格形象,又自然地滲透在整個文本的叙述之中。
作者簡介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奧地利小說家,傳記作家,出身于富裕的猶太人家庭。主要作品有《三大師傳》《象棋的故事》《昨日的世界》等。青年時代遊曆世界各地,結識羅曼·羅蘭和羅丹等人,并受到他們的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從事反戰工作,成為和平主義者,鼓吹歐洲的統一。20世紀20年代赴蘇聯,認識了高爾基。1934年遭納粹驅逐,先後流亡英國、巴西。1942年在孤寂和理想幻滅中與妻子雙雙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