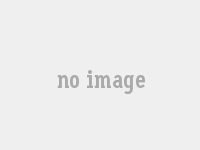内容簡介
《國語》是關于西周(公元前11世紀~公元前771年)、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時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人物、事迹、言論的國别史雜記,也叫《春秋外傳》。原來傳說是春秋末期魯人左丘明所作,與《左傳》并列為解說《春秋》的着作。近代學者研究證實,春秋時有盲史官,專門記誦、講述古今曆史。
左丘明就是稍早于孔子的著名盲史官,他講的曆史得到過孔子的贊賞。盲史官講述的史事被後人集錄成書,叫做《語》,再按照國别區分,就是《周語》、《魯語》等,總稱《國語》。西晉時曾在魏襄王墓中發現了大量寫在竹簡上的古書,其中就有《國語》三篇,談到了楚和晉的曆史,這說明戰國時此書就開始流傳了。現版本的《國語》大概是這些殘存記錄的總彙。因為是口耳相傳的零星記錄,内容主要是口語,國别和年代的區分、排列沒有嚴格标準。
全書二十一卷中,《晉語》九卷,《楚語》二卷,《齊語》隻有一卷。《周語》從穆王開始,屬于西周早期。《鄭語》隻記載了桓公商讨東遷的史實,也還在春秋以前。
《晉語》記錄到智伯滅亡,到了戰國初期。所以《國語》的内容不限于《春秋》,但确實記載了很多西周、春秋的重要事件。從傳授淵源來看,可以認為是左丘明所作。《國語》出自的記錄,是一種價值極高的原始史料,因此司馬遷着《史記》時就從中吸取了很多史料。
國語按照一定順序分國排列。在内容上偏重于記述曆史人物的言論。這是國語體例上最大的特點。
作者簡介
《國語》的作者,自古存在争議,迄今未有定論。最早提出《國語》作者為左丘明的是西漢大史學家司馬遷。他在《報任安書》中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此後東漢史學家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也記載:“《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着。”按照他們的說法,左丘明為孔子《春秋》作傳後,不幸失明,但他:“雅思未盡……稽其逸文,纂其别說……”根據作傳所剩下的材料,又編輯了一本書,即《國語》。班固、李昂等還把國語稱為《春秋外傳》或《左氏外傳》。
但是在晉朝以後,許多學者都懷疑這類說法。晉代思想家傅玄最先提出反對意見,他在《左傳·哀十三年:正義》引中言:“《國語》非左丘明所作。凡有共說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國語》虛而《左傳》實,其言相反,不可強合也。”宋人劉世安、呂大光、朱熹,直至清人尤侗、皮錫瑞等也都對左丘明着《國語》存有疑問。
宋代以來,包括康有為在内的多位學者懷疑《左傳》為西漢劉歆的僞作。
到了現代,學界仍然争論不休,一般都否認左丘明是國語的作者,但是缺少确鑿的證據。普遍看法是,國語是戰國初期一些熟悉各國曆史的人,根據當時周朝王室和各諸侯國的史料,經過整理加工彙編而成。他們認為:《國語》并非出自一人、一時、一地。它主要來源于春秋時期各國史官的記述,後來經過熟悉曆史掌故的人加工潤色,大約在戰國初年或稍後編纂成。
作品目錄
卷一周語上
卷二周語中
卷三周語下
卷四魯語上
卷五魯語下
卷六齊語
卷七晉語一
卷八晉語二
卷九晉語三
卷十晉語四
卷十一晉語五
卷十二晉語六
卷十三晉語七
卷十四晉語八
卷十五晉語九
卷十六鄭語
卷十七楚語上
卷十八楚語下
卷十九吳語
卷二十越語上
卷二十一越語下
作品影響
國語在内容上有很強的倫理傾向,弘揚德的精神,尊崇禮的規範,認為“禮”是治國之本。而且非常突出忠君思想。
國語的政治觀比較進步,反對專制和腐敗,重視民意,重視人才,具有濃重的民本思想。
國語記錄了春秋時期的經濟、财政、軍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種内容,對研究先秦時期的曆史非常重要。
藝術特色
從史學和文學成就看,《國語》不如《左傳》。但《國語》也有較為明顯的藝術特色,這就是:一、長于記言,二、有虛構故事情節。雖然在語言上較為質樸,但從文學的發展角度來看,應該說比《左傳》前進了一步。例如,《晉語》所記骊姬深夜向晉獻公哭訴進讒的事,早在秦漢之際就被人懷疑。《孔叢子·答問》記陳涉讀《國語》至此處,向博士問道:“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況國君乎?餘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為之詞。”
雖然博士曲為《國語》回護,硬說宮廷之中有女性的内史旁聽記錄,這是不能說服人的。唐人柳宗元曾寫《非〈國語〉》一文,他說:“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龐,好詭以反倫。”并說《國語》“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其實,柳宗元列舉的非難之詞,從文學的角度看,正是對《國語》應該肯定、贊美之處。
我們看越王勾踐與吳王夫差取得暫時和平之後,如何忍辱負重,蓄積力量,準備複國,作品寫得何等生動傳神:勾踐說于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仇,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于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吊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
勾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廣運百裡。乃緻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将帥二三子夫婦以蕃。”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娩)者以告,公毉守之。生文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饩;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
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其達士,絜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于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勾踐載稻與脂于舟以行。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于國,民俱有三年之食。
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于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勾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内,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仇,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複戰!”這種“十年生聚”的情景描寫得何等生動、深刻。重民如此,焉有不勝之理!
思想傾向
《國語》的思想比較駁雜。它重在記實,所以表現出來的思想也随所記之人、所記之言不同而各異,如《魯語》記孔子語則含有儒家思想;《齊語》記管仲語則談霸術;《越語》寫範蠡尚陰柔﹑持盈定傾﹑功成身退,帶有道家色彩。
《國語》與《左傳》《史記》不同,作者不加“君子曰”或“太史公曰”一類評語。所以作者的主張并不明顯,比較客觀。《國語》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禮重民等觀念。西周以來的敬天保民思想在書中得到了繼承。雖然《國語》許多地方都強調天命,遇事求神問蔔,但在神與人的關系上,已是人神并重,由對天命的崇拜,轉向對人事的重視。
因而重視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以民心的向背為施政的依據。如《魯語上》魯太史裡革評晉人弑其君厲公時,認為暴君之被逐被殺是罪有應得,咎由自取,臣民的反抗行為無可厚非。又如《周語上》邵公谏厲王弭謗中,邵公主張治民應“宣之使言”,從人民的言論中考察國家的興衰,政治的得失,國君隻有體察民情,行民之所善,去民之所惡,增加人民的财富衣食,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作品評價
就文學價值說,《國語》雖不及《左傳》,但比《尚書》《春秋》等曆史散文還有所發展和提高,具體表現為:作者比較善于選擇曆史人物的一些精彩言論,來反映和說明某些社會問題。如《周語》“召公谏弭謗”一節,通過召公之口,闡明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著名論題。《國語》在叙事方面,亦時有缜密﹑生動之筆。
如《晉語》記優施唆使骊姬讒害申生,《吳語》和《越語》記載吳越兩國鬥争始末,多為《左傳》所不載,文章波瀾起伏,為曆代傳誦之名篇。又《晉語》記董叔将娶于範氏,似絕妙的諷刺小品。所載朝聘﹑飨宴﹑辯诘﹑應對之辭。有些部分寫得較精練﹑真切。由于原始史料的來源不同,《國語》本身的文風不很統一,誠如崔述所說:“周魯多平衍,晉楚多尖穎,吳越多恣放。”(《洙泗考信錄。餘錄》)
《國語》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有目共睹。《國語》開創了以國分類的國别史體例,對後世産生了很大影響,陳壽的《三國志》、崔鴻的《十六國春秋》、吳任臣的《十國春秋》,都是《國語》體例的發展。另外,其缜密、生動、精煉、真切的筆法,對後世進行文學創作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四庫提要記載
《國語》·二十一卷(戶部員外郎章铨家藏本)
吳韋昭注。昭字弘嗣,雲陽人,官至中書仆射,《三國志》作韋曜。《裴松之注》謂為司馬昭諱也。《國語》出自何人,說者不一。然終以漢人所說為近古。所記之事,與《左傳》俱迄智伯之亡,時代亦複相合。中有與《左傳》未符者,猶《新序》、《說苑》同出劉向,而時複牴牾。蓋古人着書,各據所見之舊文,疑以存疑,不似後人輕改也。《漢志》作二十一篇。
其諸家所注,《隋志》虞翻、唐固本皆二十一卷,王肅本二十二卷,賈逵本二十卷,互有增減。蓋偶然分并,非有異同。惟昭所注本,《隋志》作二十二卷,《唐志》作二十卷。而此本首尾完具,實二十一卷。諸家所傳南北宋版,無不相同。知《隋志》誤一字,《唐志》脫一字也。前有昭《自序》,稱兼采鄭衆、賈逵、虞翻、唐固之注。今考所引鄭說、虞說寥廖數條,惟賈、唐二家援據駁正為多。《序》又稱凡所發正三百七事。
今考注文之中,昭自立義者:
《周語》凡服數一條、國子一條、虢文公一條、常棣一條、鄭武莊一條、仲任一條、叔妘一條、鄭伯南也一條、請隧一條、渎姓一條、楚子入陳一條、晉成公一條、共工一條、大錢一條、無射一條。
《魯語》朝聘一條、刻桷一條、命祀一條、郊禘一條、祖文宗武一條、官寮一條。
《齊語》凡二十一鄉一條、士鄉十五一條、良人一條、使海于有蔽一條、八百乘一條、反胙一條、大路龍旂一條。
《晉語》凡伯氏一條、不懼不得一條、聚居異情一條、貞之無報一條、轅田一條、二十五宗一條、少典一條、十月一條、嬴氏一條、觀狀一條、三德一條、上軍一條、蒲城伯一條、三軍一條、錞于一條、呂锜佐上軍一條、新軍一條、韓無忌一條、女樂一條、張老一條。
《鄭語》凡十數一條、億事一條、秦景襄一條。
《楚語》聲子一條、懿戒一條、武丁作書一條、屏攝一條。
《吳語》官帥一條、錞于一條、自亞刂一條、王總百執事一條、兄弟之國一條、來告一條、向檐一條。
《越語》乘車一條、宰一條、德虐一條、解骨一條、重祿一條。不過六十七事。合以所正訛字、衍文、錯簡,亦不足三百七事之數。其傳寫有誤,以六十為三百欤。
《崇文總目》作三百十事,又“七”字轉訛也。錢曾《讀書敏求記》,謂《周語》“昔我先世後稷”句,天聖本“先”下有“王”字;“左右免胄而下”句,天聖本“下”下有“拜”字,今本皆脫去。然所引注曰雲雲,與此本絕不相同,又不知何說也。此本為衍聖公孔傳铎所刊。如《魯語·公父文伯飲酒》一章,注中“此堵父詞”四字,當在“将使鼈長”句下,而誤入“遂出”二字下。小小舛訛,亦所不免。然較諸坊本則頗為精善。自鄭衆《解诂》以下,諸書并亡。《
國語注》存于今者,惟昭為最古。黃震《日鈔》嘗稱其簡潔,而先儒舊訓亦往往散見其中。如朱子注《論語》“無所取材”,毛奇齡诋其訓“材”為“裁”,不見經傳,改從鄭康成“桴材”之說。而不知《鄭語》“計億事,材兆物”句,昭注曰:“計,算也。材,裁也。”已有此訓。然則奇齡失之眉睫間矣。此亦見其多資考證也。
國語正義序
歸安董增齡撰
《太史公自序》:“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藝文志》:“《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着”,漢儒之說彰矣。
注釋
1.太史公自序,參見《史記.卷一百三十》。
隋劉光伯、唐陸淳、柳宗元始有異議。摭拾異同,毛舉細故,後人遂指《魯語》“皇華五善”語,言“六德”文,與《左》違。《内傳》謂魯哀公十七年“楚滅陳”、魯哀二十二年“越滅吳”,《外傳》謂吳既滅之後,尚有陳蔡之君,執玉朝越;黃池之會,《内傳》先晉人,《外傳》先吳人;《周語》自穆王至幽王,《鄭語》獨載桓武,而莊公以下無聞,皆《春秋》以前事,以傅會劉柳之說。
注釋:
1.劉炫,字光伯,隋經學家,《隋書.儒林》有傳。
2.陸淳,即陸質,《舊唐書》、《新唐書》有傳:“陸質,吳郡人,本名淳,避憲宗(李純)名改之。”
3.摭,音質,拾也。
4.毛舉細故。《漢書.刑法志》:“有司無仲山父将明之材,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鈎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诏而已。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今。”師古曰:“有司以下,史家之言也。《大雅.蒸人》(《蒸人》即《烝民》避唐太宗李世民諱)之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父将之;邦國若否,仲山父明之。'将,行也。否,不善也。言王有诰命,則仲山父行之;邦國有不善之事,則仲山父明之。故引以為美,傷今不能然也。”師古曰:“毛舉,言舉毫毛之事,輕小之甚者。塞猶當也。”
5.皇華五善。《魯語》:“《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诹、謀、度、詢,”是五善也。
然宏嗣明言《國語》之作,其文不主于經,則固不必以經為限矣,至内外《傳》同出一人,而文有異同,試以《史記》例之:《鄭世家》以友為宣王庶弟,《年表》又以友為宣王母弟;黃池之會,《晉世家》謂長吳,《吳世家》又謂長晉。遷一人之說,其不同如此。至《内傳》,則成十六年苗贲皇曰“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族”,襄二十六年聲子述苗贲皇曰“吾乃四萃于其王族”,是左氏各承晉楚兩史舊文,慎以阙疑,不敢參以臆斷也;又成十六年“塞井夷竈”二語屬之士匄,襄二十六年又屬之苗贲皇。
《内傳》一書如此,又何疑《外傳》、《内傳》之有參差乎?班氏《藝文志》言《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外傳》五十篇,《谷梁傳》十一卷,《谷梁外傳》二十一篇,則作傳者必有《外傳》以曲暢其支派。《國語》之為《左氏外傳》正同一例。《公》、《谷》二家外傳已逸,安知彼之《外傳》不與其《内傳》亦有牴牾乎?故宏嗣斷以為出左氏之手。
注釋:
1.宏嗣,即弘嗣,韋昭字弘嗣,避清高宗弘曆諱。
2.《内傳》,《春秋左傳》。
3.《外傳》,《國語》。
《内傳》之出,獻自北平侯張蒼,《外傳》不知何時始出。賈子《新書.禮容下篇》載單靖公、單襄公事,皆采《國語》,則《國語》之出,亦當在漢文帝之世。《儒林傳》載賈生治《春秋左氏傳》,今又兼述《國語》,則賈生亦以《内傳》、《外傳》之同出《左氏》也。班氏《藝文志》既載《國語》二十一篇,又載《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所分,則漢時《國語》有兩本,今所傳二十一篇與班《志》合。
然《公羊疏》第六卷引《國語》曰“懿始受谮而烹哀公”,《公羊疏》第二十一卷引《國語》曰“專諸膳宰,僚嗜炙魚,因進魚而刺之”,《史記?夏本紀》裴骃《集解》引《國語》曰“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豫章”,《水經·河水》注引《國語》曰“華嶽,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蕩腳蹋,開而為兩,今掌足之迹仍存”。
《水經·瓠子河》注引《國語》曰“曹沫挾匕首劫齊桓公返遂邑”,《史記·補三皇本紀》索隐引《國語》曰“伏羲風姓”,《夏本紀》正義引《國語》曰“滿于巢湖”,《鄒魯列傳》索隐引《國語》曰“楚人卞和得玉璞”,《禮·祭法》疏引《國語》曰“神農之子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文選·東京賦》注引《國語》曰“分魯公以少帛綪茷”,《文選》盧谌《贈劉琨詩》注引《國語》曰“齊大夫子高适魯,見孔子曰:‘而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之為大也。’”今本皆無之,則逸者不少矣。
然裴骃引“敷淺原”一條,郦道元引“華嶽”一條,《文選》注引“子高”一條,其文與《國語》絕不類,議者疑之。《齊語》一篇皆《管子·小匡篇》之辭,《管子》遠出《左氏》之前,必不預知《國語》之文而襲之,竊疑《齊語》全亡,而後人采《小匡》以補之與?說者又謂《越語》下卷,疑非《國語》本文,其與他卷不類。又《國語》敍事,雖不盡有年月,然未嘗越次,今上卷已書越滅吳,下卷複從句踐即位三年起,他國無此例。《内傳》無範蠡姓名,《外傳》止《吳語》一見,在五大夫之列,旅進旅退而已,至此卷乃專載蠡策,若滅吳之事,蠡獨任之者,殊非事實。
《藝文志·兵權謀》有《範蠡》二篇,此殆其一,但攙入當在劉向以前。齡案:孔晁本二十卷,則第二十一卷,孔博士已不信其《國語》真文矣。宋公序《補音》本及天聖本兩家并行,近曲阜孔氏所刻用《補音》本。今兼收二家之長,而用《補音》本者十之七八雲。為之注者,有漢鄭衆、賈逵,魏王肅,吳虞翻、唐固、韋昭,晉孔晁七家。今唯韋解尚存,然已間有逸者,如《禹貢》疏引韋解雲“以文武侯衛為安王賓之,因以為名”,《文選?東京賦》注引韋解雲“綪茷,大赤也”,今本皆無之。
鄭注則他書征引者僅有數條。其馀四家賈、王、虞、唐除韋所引外,則《史記》集解、索隐、正義、《詩》疏、《周禮》疏、《春秋左傳》疏、《公羊》疏征引為多。孔出韋後,亦見于諸疏及《史記》注。今皆采掇,以補宏嗣之義。
《韋解》孤行天壤間,已千五百馀年,未有為之疏者。竊意許叔重、鄭康成兩君,為漢儒宗主,自三國分疆,而儒學為之一變,宏嗣生于江南擾攘之秋,抱阙守殘,視東漢諸儒已非其時矣,其所解固援經義,而與許鄭諸君,有未翕合者,依文順釋,義有難安,況墨守一家之說,殊非實事求是之心,用是采撷諸經舊說,間下己意,非求争勝于青藍,不敢面谀夫鹿馬。檢楊氏《谷梁正義》間與範氏之注語具抑揚,則知疏不破注之例,古人亦所不拘。今铨釋韋解之外,仍援許鄭諸君舊诂,備載其後,以俟辨章。譬導水而窮其源,非落葉而離其根也。
韋解體崇簡潔,多阙而不釋,《史記》集解、索隐、正義,及應劭、如淳、晉灼、蘇林、顔師古等家《漢書》注、章懷太子《後漢書》注,凡于馬、班正文采取《國語》者,各有發揮,或與韋解兩歧,或與韋解符合,同者可助其證佐,異者宜博其旨歸,并采兼收以彙古義。錞鼓不同音,而皆悅耳;荼火不同色,而皆美觀也。國邑、水道,以《漢.地理志》、《後漢.續郡國志》為主,而參以《水經注》、《元和郡縣志》、杜氏《通典》諸家,并列我朝所定府廳州縣之名,庶覽者了然。至于宮室器皿衣裳之制度,則孔賈諸疏具存,止撷簡要,不事詳叙。
唯是賦性颛愚,疏于搜讨,況草茅孤陋,既不獲窺秘府鴻章,廣資聞見,又不獲交四方碩彥,共得切磋,固蔽是虞,未敢自信。今年逾四十,平日所聞于師友者,恐漸遺忘,是以就已撰集者,寫錄成編。奮螳蜋之臂,未克當車;矢精衛之誠,不忘填海。歲在阏逢閹茂,始具簡編。時經五稔,草創初成。勉出所業,就正君子。倘披其榛蕪,匡其缪誤,俾得自知其非,庶免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責,則重拜大贶,感且不朽矣!
曆代研究
注釋本
《國語》成書以來,東漢鄭衆、賈逵,魏晉王肅、唐固、虞翻、韋昭、孔晁等為之作注。唐宋以來,各家之注多亡佚,惟韋昭《國語解》存于世。北宋時,宋庠(字公序)曾整理《國語》及韋解,并作《國語補音》三卷。然其間亦有宋庠不知者:如後漢楊終撰有《改定春秋外傳章句》,三國孫炎撰有《國語》注,北魏劉芳撰有《國語音》一卷。公序雲:“先儒未有為《國語》音者,蓋外、内傳文多相涉,字音亦通故也。然近世傳《舊音》一篇,不箸撰人姓名,尋其說,乃唐人也。”恐失檢于《魏書·劉芳傳》。除此以外,我們不排除東漢、三國、魏晉之間佚名舊注大量存在而後世散佚不傳這種情況。
韋昭《國語解》是現存于世的《國語》最早注本,他在《國語解叙》中對其之前的注家及其作注的緣由、依據也有清楚的說明:“遭秦之亂,幽而複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于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謬。至于章帝,鄭大司農為之訓注,解疑釋滞,昭析可觀,至于細碎,有所阙略。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為已憭矣,然于文間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間,故侍禦史會稽虞君,尚書仆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為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理釋,猶有異同。
昭以末學,淺暗寡聞,階數君之成就,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諸家并行,是非相貿,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切不自料,複為之解。因賈君之精實,采虞、唐之信善,亦以所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内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為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他的大體情況上文已述。
公序以下直至清初,研究《國語》者寥寥無幾。有清一代,樸學大興,其間不乏校注《國語》者。主要有:汪遠孫《國語校注本三種》(《國語三君注輯存》、《國語發正》、《國語明道本考異》),陳瑑《國語翼解》,董增齡《國語正義》等。
汪遠孫《國語校注本三種》對《國語》文本作了系統翔實的研究。其作《國語校注本三種》的緣起、體例、依據在《三種》各自序言都有明确交代。茲錄于下,以資參證。
《國語三君注輯存》序:“三君者,後漢侍中賈君逵、吳侍禦史虞君翻、吳尚書仆射唐君固也。韋宏嗣采摭三君,并參己意,成《國語解》二十一卷。漢章帝時,鄭大司農衆作章句,其書最為近古,久亡其篇數。魏中領軍王肅、晉五經博士孔晁亦為章句訓注,後先于韋而解不載。今遠孫不揣谫陋,搜羅舊聞,其三君說有見于解中有不見于解中悉錄之,王、孔諸家亦載焉。于以識韋氏作解之去就、而衆說之足資取益也。“《國語》稱三君者,仍宏嗣之本書也。”
《國語發正》序:向稱《外傳》,與《内傳》相為表裡,綜述義文,說家輩出。自漢迄晉,散佚無存。今所完存者,唯韋氏注而已。注中都采古訓,又參幷己意。實事求是,卓爾钜觀。然學道無窮而偏漏難掩,此中得失,間有瑜瑕,可資考訂。去就需才,遠孫妄不自揣,研慮多年,搜輯舊聞,博取通語,苟可明者,皆收錄焉。抑有疑者,必備參焉。解訛者駁之,義缺者補之,辭意有未昭晰者複詳說之。爰列三例,依傳作卷,為《發正》:二十一卷,所以發其疑而正其似也。”
《國語明道本考異》“舊題天聖明道本《國語》,天聖,宋仁宗年号;明道,乃仁宗改元。卷末署雲‘天聖七年七月二十日開印,明道二年四月初五日得真本’。是明道二年以天聖印本重刊也。近代盛行宋公序《補音》,明人許宗魯、金李皆從公序本重刊。兩本各有優劣,而後是非異同判焉。今刻以明道本出大字,公序本輔行小字于下,它書所引之異文及諸家所辨之異字,亦皆慎擇而采取之。讀《國語》者庶乎知其異而是非可識也。”
《國語校注本三種》(《國語三君注輯存》、《國語發正》、《國語明道本考異》),有清道光丙午閏五月汪氏振绮堂刊本。其中《國語發正》被王先謙收入《清經解續編》,《國語明道本考異》收入《四部備要》,列于黃丕烈《重刊明道二年〈國語〉》、《校刊明道本韋氏解〈國語〉劄記》之後。
陳瑑《國語翼解》,主要是搜集相關文獻對韋昭《國語解》作疏證補充工作。顧其名即知其作是書之旨,翼者,輔也,佐也,助也。《廣雅書局叢書》、《叢書集成初編》均有收入。
董增齡《國語正義》,其序雲:“宋公序補音本及天聖本兩家并行,近曲阜孔氏所刻用補音本。今兼收二家之長,而用補音本者十之七八。……雲為之注者,有漢鄭衆、賈逵、魏王肅、吳虞翻、唐固、韋昭,晉孔晁七家,今唯韋解尚存。……今铨釋韋解之外,仍援許鄭諸君舊诂備載其後,以俟辯章。譬導水而窮其源,非落葉而離其根也。韋解體崇簡潔,多阙而不釋。
《史記》集解、索隐、正義及應劭、如淳、晉灼、蘇林、顔師古等家《漢書注》、章懷太子《後漢書》注,凡與馬班正文采取《國語》者,各有發揮。或與韋解兩歧,或與韋解符合。同者可助其左證,異者宜博其旨歸。并采兼收,以彙古義。錞鼓不同音,而皆悅耳;荼火不同色,而皆美觀也。國邑水道,以《漢·地理志》、《後漢·續郡國志》為主,而參以《水經注》、《元和郡縣志》、杜氏《通典》,諸家并列。我朝所定府廳州縣之名庶覽者了然。至宮室器皿衣裳之制度,則孔賈諸疏具存,止撷簡要,不事詳叙。”
正義者,注之疏也。殆因“疏不破注”之例,《國語正義》雖篇幅不小,但發明無多。吳曾祺在其《國語韋解補正》叙中就說:“然董氏之書,多征引舊典,而于文義之不可通者,反忽而不及。似博而實略,似精而實疏。”這個評判應該說是相當公允的。董增齡《國語正義》有清光緒庚辰章氏式訓堂刊本,巴蜀書社1985年據此本影印出版了影印本。
此外,清人對《國語》還作了大量輯佚工作:王仁俊《經籍佚文》輯有《國語佚文》一卷;王谟《漢魏遺書鈔》、勞格《月河精舍叢鈔》、黃奭《漢學堂叢書》、《黃氏逸書考》、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蔣曰豫《蔣侑石遺書》、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對已亡佚的東漢鄭衆、賈逵,魏晉王肅、唐固、虞翻、孔晁等《國語》注作了輯佚工作。這些輯佚工作,作用不言自明。
清末校诂《國語》者有吳曾祺,撰有《國語韋解補正》一書。他在《國語韋解補正》叙中說:“《國語》一書,時有箋疏,惜其寥寥無幾。獨高郵王氏,所得為多。乃擇其說之合者,悉纂而輯之。其有不足,辄以己意謬為附益。歲月既久,楮墨遂滋。因彙為一編,名之曰《國語韋解補正》。補者,補其所未備;正者,正其所未安。備且安,是書之本末具矣。”其書亦間有創獲,于讀《國語》者,不無裨益。清宣統元年,商務印書館初版其書。民國年間,商務印書館有數次印行。
其後沈镕有《國語詳注》,惟存《國語》正文,摘列重要詞句略加诠釋,其性質為重注而非補注。因其發明無多,後人稱引亦少。其書民國五年文明書局有鉛印本,民國二十四年文明書局曾再次印行。
另有金其源《讀書管見·國語》(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時有所得。
台灣學者張以仁《國語斠證》一書,摘錄有異文、疑義之相關語句,以天聖明道本、公序本、公序《〈國語〉補音》、董增齡《國語正義》本等本相互雠校,旁參黃丕烈《劄記》、汪遠孫《考異》等諸家成說,廣采古注、類書及相關書中材料,以理其訛脫,正其謬誤。其于《國語》,厥功甚偉。此書由台灣商務印書館于1969年印行。
在《國語》校注本中,徐元诰《國語集解》,行世最晚,在韋解之下而能網羅之前王引之、汪中、劉台拱、黃丕烈、汪遠孫、陳瑑、董增齡、吳曾祺、沈镕各家之說,并于諸說紛存、文有疑義處以“元诰按”明其取舍,于讀《國語》者甚為便利,可稱當前《國語》校注本之最佳者。
但王樹民先生在《國語集解》點校前言裡有中肯地評價:“《國語集解》之編撰方式雖善,但其編撰工作則甚為粗疏,成為其書之最大缺陷。”其書1930年曾由中華書局印行。2002年,中華書局又出版了經王樹民、沈長雲二先生點校的《國語集解》。每卷之後,都附有點校者所作校記,在最大程度上彌補了徐元诰《國語集解》編撰工作粗疏而導緻的訛誤。2006年修訂本附上了人名索引。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校點《國語》,以《四部備要》收錄的士禮居翻刻明道本《國語》為底本,參校《四部叢刊》影印明代翻刻公序本,并吸收了一些前人的校勘成果,略加按語,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後又修訂重版多次。此為目前最易得之本,且閱讀甚為便利。
選譯本
葉麟《白話譯解國語》(屬于選譯),大連大達書社1935年
秦同培注釋、宋晶如增訂《廣注語譯國語精華》(屬于選譯),世界書局,初版不可考,新一版出版于1943年
傅庚生《國語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該書的影響比較大,在後來的《國語》譯注中經常可以看到《國語選》的影子。
高振铎、劉幹先《國語選譯》,巴蜀書社1990年
全譯本
《國語》的權威點校本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點校本,後來的《國語》譯注本都以其為底本、參酌他本而成。
薛安勤、王連生《國語譯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
汪濟民等《國語譯注》,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2年
董立章《國語譯注辨析》,暨南大學出版社1993年
邬國義、胡果文等《國語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李維琦《白話國語》,嶽麓書社1994年
黃永堂《國語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該書發行量較大,影響較廣。
秦峰《譯注國語》,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
趙望秦、張豔雲等《白話國語》,三秦出版社1998年
來可泓《國語直解》,複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
鮑思陶點校《國語》,齊魯書社2005年
曹建國等《國語簡注通說》,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
《國語》的版本系統
《國語》的版本系統非常簡單清晰,即明道本與公序本兩個系統。
黃丕烈在《校刊明道本國語劄記》叙中說:“《國語》,自宋公序取官私十五六本校定為《補音》,世盛行之,後來重刻,無不用以為祖。”經宋庠整理之本,此後成為主要傳世之本:公序本。其後明嘉靖戊子金李刊澤遠堂本(或稱金李本)即翻刻自公序本,世稱善本,而明道本又罕為世人所見,故此金李本就成了明清以來絕大多數本子的實際祖本。
黃丕烈《校刊明道本國語劄記》叙雲:“如此明道二年本者,乃不絕如線而已。”(國學基本叢書選印《國語》,頁二四一,上海書店1987年版)又《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二錢大昕序雲:“荛圃得是書而寶之,又欲公其寶于斯世。”(國學基本叢書選印《國語》錢大昕序,上海書店1987年影印出版。)可見明道本之罕見。《國語》(含《補音》)版本現存情況,可詳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上冊),第207~21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國語》之存于今者,以宋明道二年椠本為最古。”汪遠孫《國語明道本考異序》雲:“舊題天聖明道本《國語》,天聖,宋仁宗年号;明道,乃仁宗改元。卷末署雲‘天聖七年七月二十日開印,明道二年四月初五日得真本’。是明道二年以天聖印本重刊也。”黃丕烈《校刊明道本國語劄記》叙又雲:“有未經其(指宋庠)手,如此明道二年本者,乃不絕如線而已。……丕烈深懼此本之遂亡,用所收影鈔者,開雕以饷世。其中字體,前後有歧,不改畫一,阙文壞字,亦均仍舊。無所添足,以懲妄也。”自此,明道本才得以廣為流傳。
自清中期以後,明道本與公序本同為《國語》通行之本。《四部叢刊》本《國語》是據嘉靖戊子金李澤遠堂本影印,而《四部備要》本《國語》則據黃丕烈《重刊明道二年〈國語〉》排印,其後附有黃丕烈《校刊明道本韋氏解〈國語〉劄記》、汪遠孫《國語明道本考異》。《四部叢刊》本、《四部備要》本為易得且又可靠的兩個版本。《國語》之本,非此即彼,或以其一為底本、其一作參校。
國語研究
《國語》相傳為春秋末年魯國人左丘明所作,是先秦時期一部重要的文獻。《國語》記錄了春秋時期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文化等諸方面内容,保存了不少先秦時期的曆史傳說、政治制度和宗教祭祀方面的材料。一定程度上,《國語》資料來源複雜,八《語》思想内容特點,故《國語》研究不應拘泥于文體學條框。利用傳統考據和曆史文獻學的方法,逐一考察《國語》的成書、内容、思想、文體、文學成就等問題,從而揭示《國語》所兼有的曆史、文學、經學、政教的多重問題。
近年來,學術界對《國語》的研究雖有充分的重視,但全面系統深入的研究着作還略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