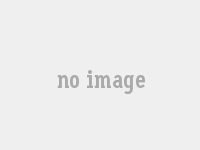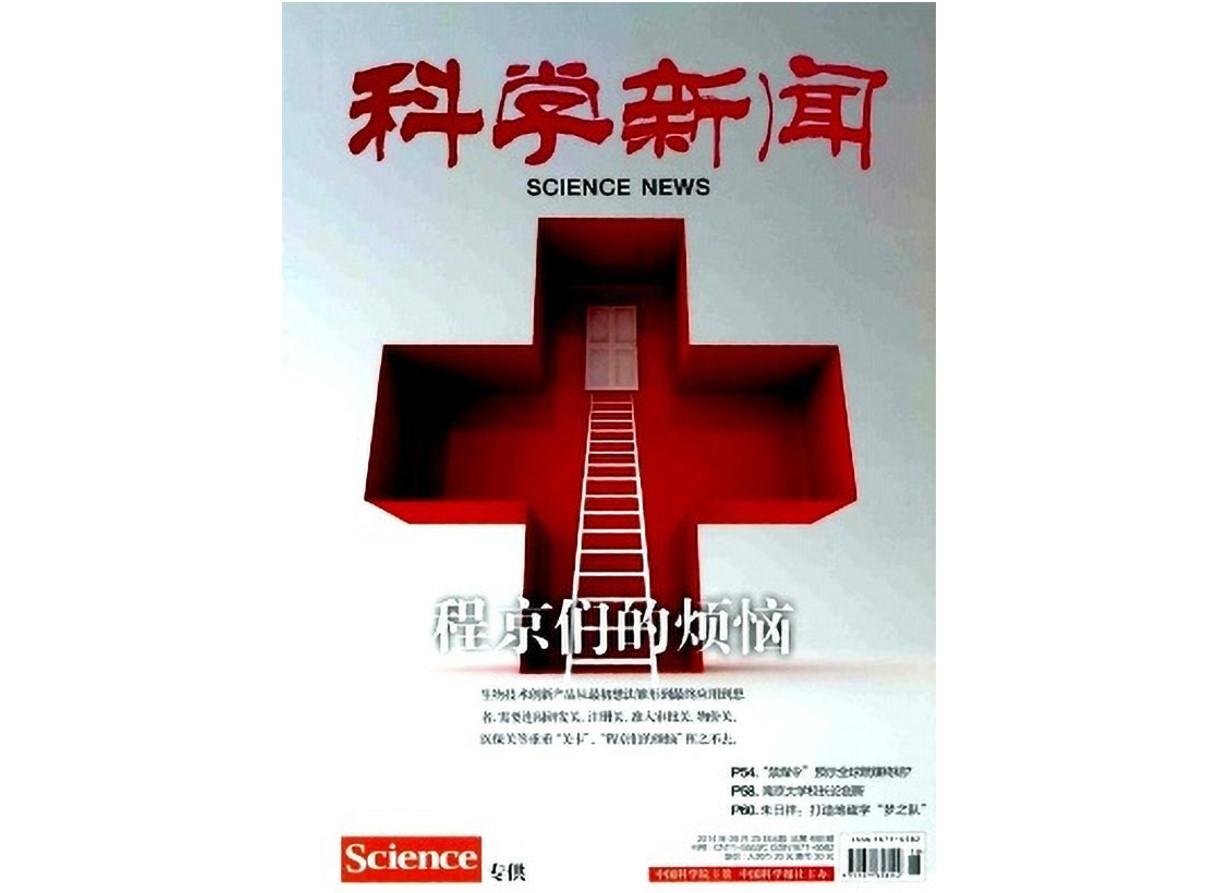通鑒記載
神宗體無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熙甯元年(遼鹹雍四年)。
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诏改元。
複命武臣同提點刑獄。
丙子,遼主如鴛鴦泺。
丁醜,以旱減天下囚罪一等,杖以下釋之。
辛巳,遼改易州兵馬使為安撫使。
丁亥,命宰臣極言阙失。
遼主獵于炭山。
庚寅,禦殿,複膳。
辛卯,遼遣使赈西京饑民。
壬辰,帝幸寺觀祈雨。
參知政事趙概數以老求去,丙申,罷知徐州。概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惡,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利物者為多,時議比之劉寬、婁師德。
以三司使唐介參知政事。故事,執政坐待漏舍,宰相省閱所進文書,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預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以為常。
丁酉,诏修《英宗實錄》。
壬寅,诏太學增置外舍生百員。初,太學置内舍生二百員,官為給食。至是待次蓋百馀人,谏官以為言,故有是诏。
二月,甲辰朔,遼命元帥府募軍。
辛亥,令諸路每季以雨雪聞。
乙卯,以孔宗願子若蒙為新泰縣主簿,襲封衍聖公。
初,言者交論種谔擅興生事,诏系長安獄。谔乃悉焚當路所與簡牍,置對,無一語罣人,惟自引伏。丙辰,貶谔秩四等,安置随州。
司馬光進讀《資治通鑒》,至蘇秦約六國從事,帝曰:“蘇秦、張儀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對曰:“縱橫之術,無益于治。臣所以存其事于書者,欲見當時風俗,專以辯說相高,人君悉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複邦者也。”帝曰:“聞卿進讀,終日忘倦。”
帝謂文彥博等曰:“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韓绛曰:“為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帝曰:“大抵威克厥愛,乃能有濟。”
丁卯,遼主巡行北方。
三月,癸酉朔,帝謂文彥博等曰:“當今理财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宜共留意節用。”又曰:“漢文身衣弋绨,非徒然也,蓋亦有為為之耳,數十年間,終有成效。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
庚辰,夏遣薛宗道等來告哀。帝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先已執送之矣。”乃賜诏慰之,并谕令上大首領數人姓名,當爵祿之,俟李崇貴至,即行冊禮。及崇貴至,雲:“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鑒及金銀物。”初,定之歸,上其劍、鑒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為定賣己,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崇貴等罪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
夏亦遣使告哀于遼,遼遣人吊祭。
甲申,遼赈應州饑民。
先是遼禁南京種稻,民病之。乙酉,命除軍行之地,并許民種稻。
丙戌,诏恤刑。
戊子,作太皇太後慶壽宮,皇太後寶慈宮。
庚寅,遼赈朔州饑民。
乙未,诏河北轉運司預計置赈濟饑民。
丁酉,潭州雨毛。
夏,四月,壬寅朔,新判汝州富弼入見,以足疾,許肩輿至殿門。帝特為禦内東門小殿見之,令其子紹庭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至日昃,問以治道。弼知帝銳于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奸人得以傅會其意。陛下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随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
又問邊事,弼曰:“陛下臨禦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幹戈一起,所系禍福不細。”帝默然良久。又問為治所先,弼曰:“阜安宇内為先。”帝稱善,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弼力辭,赴郡。
乙巳,诏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安石素與韓绛、韓維及呂公着相友善,帝在籓邸,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辄曰:“此維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為太子庶子,又薦以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命知江甯府;數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至是始造朝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
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于君矣。”
又問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緻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書,其略曰:“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托,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将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内以平中國。于是除苛政,止虐刑,廢強橫之籓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天下先,其于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
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讨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
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格叙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将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于考績;而遊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于庸人。
農民壞于差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于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為之擇将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于理财,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勤憂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于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伏惟陛下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急,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明日,帝謂安石曰:“昨閱卿奏書,所條衆失,卿必已一一經畫,試為朕詳言施設之方。”安石曰:“遽數之不可盡,願陛下以講學為事,講學既明,則施設之方不言而自喻矣。”
辛亥,同天節,群臣及遼使初上壽于紫宸殿。
禮官議,欲用唐故事,以五月朔請禦大慶殿受朝,因上尊号。翰林學士呂公着言:“五月會朝,始于唐德宗,取術數厭勝之說,憲宗以不經罷之。況尊号非古典,不系人主重輕。”陛下方追複三代,何必于陰長之日為非禮之會,受無益之名!”從之。
戊午,回鹘貢于遼。
庚申,呂公着、王安石等言:“故事,侍講者皆賜坐;自幹興以來,講者始立,而侍者皆坐聽。臣等竊謂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坐。”禮官韓維、刁約、胡宗愈言:“宜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劉分攵曰:“侍臣講論于前,不可安坐。避席言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
龔鼎臣、蘇頌、周孟陽、王汾、韓忠彥皆同分攵議,曰:“幹興以來,侍臣立講,曆仁宗、英宗兩朝,行之且五十年,豈可輕議變更!”帝問曾公亮,公亮曰:“臣侍仁宗書筵亦立。”後安石因講賜留,帝面谕曰:“卿當講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
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禦史台劉敞卒。敞學問淵博,寝食坐卧,未嘗不以《六經》自随。嘗得先秦彜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按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
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歐陽修每于書有疑,折簡來問,敞對使答之,筆不停手,修辄歎服。慶曆以前,學者守注疏之說,至敞為《七經小傳》,始民諸儒異。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于敞,而新奇抑又甚矣。
癸亥,以孫覺為右正言、同知谏院。帝與覺言,欲革積弊,覺曰:“弊固不可以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帝稱其知理。
五月,癸酉,帝謂文彥博等曰:“丁渭、王欽若、陳彭年何如人?”彥博等各以所聞對,因言:“當時修建宮殿,皆謂等開之,耗祖宗積儲過半,至今府庫不複充實。”帝曰:“王旦為宰相,不得無過。”韓绛曰:“旦嘗谏,真宗不從;求去位,又弗許。”帝曰:“事有不便,當極論列,豈可以求去塞責??”
國子監言補試國子監生以九百人為額,從之。
甲戌,募饑民補廂軍。
庚辰,诏兩制及國子監舉諸王宮教授。
丙戌,遼主駐特古裡。
戊戌,廢慶成軍。
六月,癸卯,錄唐魏征、狄仁傑後;從韓琦請也。
丁未,占城來貢。
辛亥,诏:“諸路監司訪尋州縣,興複水利,如能設法勸誘修築塘堰、圩堤,功利有實,當議旌寵。”
壬子,遼西北路雨谷三十裡。
乙卯,賜知唐州高賦敕書獎谕。賦在唐五年,比罷,增戶萬一千有奇,辟田三萬馀頃,歲益稅二萬二千有奇,作陂堰四十有四。
是月,河溢恩州烏欄堤,又決冀州棗強埽,北注瀛州之域。
秋,七月,壬申,遼署烏庫德?寽勒部都統軍司。
癸酉,诏:“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者,從謀殺減二等論。”初,登州奏,有婦阿雲,母服中聘于韋,惡韋醜陋,謀殺韋,傷而不死。及按問,欲舉自首。審刑院、大理寺論死,用違律為婚奏裁,敕貸其死。知登州許遵奏,引律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以謀為所因,當用按問欲舉條減二等;刑部定如審刑、大理。
時遵方召判大理,禦史台劾遵,而遵不伏,請下兩制議,乃令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安石以謀與殺為二事,光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為所由,與殺為二,則故與殺亦可為二邪?”二人議不同,遂各為奏,光議是刑部,安石議是遵。诏從安石議。
乙亥,名秦州新築大甘谷口砦曰甘谷城。初,秦州生戶為諒祚劫而西徙,有空地百裡,名筚篥,知州馬仲甫請城而耕之,即大甘谷口砦也。至是特賜名。
丙子,遼主獵于黑嶺。
丁醜,诏:“諸路帥臣、監司及兩制、知雜禦史已上,各舉武勇謀略三班使臣二人。”
賜布衣王安國進士及第。安國,安石弟也,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為第一,以母喪不試,廬墓三年。韓绛薦其材行,召試,賜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
己卯,群臣表上尊号曰奉元憲道文武仁孝,诏不許。及第三表,司馬光入直,因言:“尊号之禮,非先王令典,起于唐武後、中宗之世,遂為故事。先帝不受尊号,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書信,彼有尊号而我獨無,以為深恥,于是群臣複以非時上尊号。
昔漢文帝時,匈奴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複為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号。”帝大悅,手诏答光曰:“非卿,朕不聞此言。”遂終不許。
以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知越州陳升之知樞密院事。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并置,時文彥博、呂公着既為使,帝以升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故特命之。
辛巳,孫覺責授太子中允,仍知谏院。先是陳升之登對,帝面許擢置中樞。而覺相繼登對,帝因與言。“升之宜居宥密;邵亢不才,向欲使守長安,而宰相以為無過。”時升之已有成命,而覺不知,退即上言:“宜使亢知永興,升之為樞密使。”帝以覺為希旨收恩,故責之。覺又言滕甫貪污頗僻,斥其七罪,帝不信,以覺疏示甫,甫謝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
壬午,以恩、冀州河決,賜水死家缗錢及下戶粟。
甲申,京師地震。乙酉,又震,大雨。是夜,月食,有司言《明天曆》不效,當改;诏司天更造新曆。
知開封府呂公着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緻福,或簡誣以緻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盡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唯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為邪說所亂。顔淵問為邦,孔子以遠佞人為戒。蓋佞人唯恐不合于君,則其勢易親;正人唯恐不合其義,則其勢易疏。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
辛卯,以河朔地大震,命沿邊安撫司及雄州刺史候遼人動息以聞。賜壓死者缗錢。
京師地又震。
壬辰,遣禦史中丞滕甫、知制诰吳充安撫河北。時河北地大震,湧沙出水,破城池廬舍,吏民皆幄寝茇舍。甫至,獨卧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饑者,除田稅,察惰吏,修堤防,繕甲兵,督盜賊,北道遂安。
韓琦自永興複請相州以歸。會河北地數震,知梓州何郯因上書言陰盛臣強以譏切琦,又乞召還王陶,以迎合上意,帝薄之。後陶入為三司使,遷翰林學士,中丞呂公着複論“陶賦性傾邪,當韓琦秉政,谄事無所不至;及為中丞,及誣琦以不臣之迹,陷琦以滅族之禍。反複如此,豈可信任!”乃出陶知蔡州。
癸巳,疏深州溢水。
甲午,減河北囚罪一等。
丁酉,降空名诰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民入粟。
戊戌,知谏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饑河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乞自今,宮禁遇聖節,恩賜度牒,并裁損或減半為紫衣,稍去剃度之冗。”從之。
是月,河溢瀛州樂壽埽。
遼南京霖雨,地震。
八月,壬寅,京師地又震。
同知谏院孫覺既降官,累章求出,不許。覺以為去歲有罰金禦史,今茲有貶秩谏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可居位者也,乃出覺通判越州。
诏京東、西路存恤河北流民。
甲辰,京師地又震。
辛亥,迩英講讀已,召司馬光,問以河北災變,光對曰:“饑馑之歲,金帛無所用,惟食不可一日無耳,宜多漕江、淮之谷以濟之。”帝因論治道,言州縣長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擇。光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馀州,責其精擇誠難,但能擇十八路監司,使之擇所部知州而進退之,知州擇所部知縣而進退之,得人多矣。”又問:“谏官難得人,誰可者?”對曰:“凡擇言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得。鹽鐵副使呂誨、侍禦史吳景,此兩人似堪其選也。”
癸醜,曾公亮等言:“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司馬光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王安石曰:“昔常衮辭堂馔,時議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光曰:“衮辭祿,猶賢于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所以不足者,由未得善理财之人耳。”光曰:“善理财之人,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财。
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财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國用足,不過設法以陰奪民利,其害甚于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史遷書之,以見其不明耳。”争論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亦不複辭。
乙卯,降空名诰救付河東及鄜延路安撫司,募民入粟實邊。
帝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甲子,诏中書門下:“考太祖之籍,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于郊廟,世世勿絕。”
乙醜,複行《崇天曆》。
以鹽鐵副使呂誨為天章閣待制,複知谏院;用司馬光言也。
诏:“自今試館職,并用策論,罷詩賦。”
九月,同知太常禮院劉分攵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當自奉其國之祖。太祖傳天下于太宗,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别為置後。若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至矣。”從之。辛未,泾州觀察使舒國公從式進封安定郡王。從式,德芳之孫也。
初,韓琦自永興入觐,言于帝曰:“推崇太祖之後,令擇一人封王,常從獻于郊廟,不知何故及此?自古主鬯從獻,皆太子事;今忽擇一人令郊廟從獻,豈不疑駭天下視聽乎!”帝悟,遂罷從獻之旨。
丁亥,減後妃、臣僚薦奏推恩。
戊子,莫州地震,有聲如雷。
丁酉,诏三司裁定宗室月料,嫁娶、生日、郊禮給賜。
己亥,遼主駐借絲澱。
先是王安石講《禮記》,數難記者之非是,帝以為然,冬,十月,壬寅,诏講筵權罷講《禮記》。是日,帝留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議論。”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契;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
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稷、契、傅說之賢,亦将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上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兇。”安石曰:“惟能辨四兇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兇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丙午,帝問講讀官富民之術,司馬光言:“富民之本在得人。縣令最為親民,欲知縣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轉運使。陛下但能擇轉運使,俾轉運使案知州,知州案縣令,何憂民不富也!”
辛亥,遼曲赦南京徙罪以下囚。以永清、武清、安次、固安、新城、歸義、容城諸縣并遭水災,複一歲租。
乙卯,出奉宸庫珠,付河北買馬。
戊辰,禁銷金服飾。
遼遣使冊李秉常為夏國王。
十一月,癸酉,太白晝見。
丙戌,朝飨太廟,遂齋于郊宮。丁亥,祀天地于圜丘。
先是河溢恩、冀、深、瀛之境,帝憂之,以問近臣司馬光等。都水監丞李立之,請于四州創生堤三百六十七裡以禦河,而河北都轉運司言當用夫八萬三千馀人,役一月成,今方災傷,願徐之。都水監丞宋昌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河港進約,簽入河身,以纾四州水患,遂與屯田都監内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于是都水監奏:“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溢,緻上下埽岸屢危。今棗強抹岸沖奪故道,雖創新堤,終非久計。
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而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黃、禦河一帶北行,經邊界,直入水海,其流深闊,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是未嘗睹黃河在界河内東流之利也。”至是诏光及入内副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視六塔、二股利害。甲午,光入辭,因請河陽、晉、绛之任,帝曰:“汲黯在朝,淮南寝謀,卿未可去也。”
乙未,京師及莫州地震。
十二月,壬寅,诏:“自今内批指揮事,俟次日複奏行下。”
癸卯,瀛州地大震。
庚戌,賜夏國主嗣子秉常诏:“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冊,并以綏州給還,所有歲賜,自封冊後,并依舊例。”
辛亥,錄唐段秀實後。
夏遣使貢于遼。
庚申,以判汝州富弼為集禧觀使,诏乘驿赴阙。
辛酉,邵亢罷。亢在樞密逾年,無大補益,帝頗厭之。至是引疾求去,遂出知越州。
是歲,前建昌軍司理參軍德安王韶,詣阙上《平戎策》三篇,其略曰:“國家欲平西賊,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族。蓋招撫沿邊諸族,所以威服角氏也;威服角氏,所以脅制河西也。陛下誠能擇通材明敏之士、周知其情者,令往來出入于其間,推忠信以撫之,使其傾心向慕,歡然有歸附之意,但能得大族首領五七人,則其馀小種,皆可驅迫而用之。
諸種既失,角氏敢不歸”角氏歸,即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急之可以蕩複其巢穴,緩之可以脅制其心腹,是所以見形于彼而收功在此矣。今瑪爾戬諸族,數款塞而願為中國用者久矣,此其意欲假中國爵命以威其部内耳。而邊臣以棟戬故,莫能為國家通恩意以撫之,棄近援而結遠交,貪虛降而忘實附,使棟戬得市利而邀功于我,非制勝之利也。瑪爾戬諸族皆角氏子孫,各自屯結,其文法所及,遠者不過四五百裡,近者二三百裡,正可以并合而兼撫之。臣愚以為宜遣人往河州與瑪爾戬計議,令入居武勝軍或渭源城,與漢界相近,輔以漢法。
因選官一員有文武材略者,令與瑪爾戬同居,漸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羌,有不從者,令瑪爾戬挾漢家法令以威之。其瞎征、欺巴溫之徒,既有分地,亦宜稍以爵命柔服其心,使習用漢法,漸同漢俗,在我實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不得與諸羌結連,此制賊之上策也。”初,韶試制科不中,客遊陝西,訪采邊事甚悉,故為是書以奏。帝異其言,召問方略,以韶管句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
夏改元幹道。
曆史大事
梁氏聽政
幹道元年(1068)正月秉常繼位時,年僅八歲。其母恭肅章憲皇太後梁氏聽政,總攬朝廷内外一切大權。緊接着梁氏又迅速提拔自己的弟弟梁乙埋,并将朝中大權全部拱手送給了梁乙埋。梁乙埋擔任國相後,立即提拔他的子弟親戚占據西夏政權的各個要害部門,于是梁氏一家逐漸勢焰熏天,控制了西夏政權。
塔裡幹之亂
鹹雍五年(1068)正月,阻蔔部(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境)首領之一塔裡幹起兵反抗遼朝的殘暴統治,消息傳到遼朝京城後,遼道宗急忙任命晉王耶律仁先為西北路招讨使,同時将鷹紐印和佩劍交給耶律仁先,耶律仁先可以憑大印和寶劍先斬後奏。其後遼興宗又任命知殿前都點檢蕭汗魯為行軍都監,率領遼朝大軍深入阻部落腹地,讨伐塔裡幹。
遼軍迅速推進,俘虜了許多塔裡幹的人馬,耶律仁先在行軍過程中,嚴格烽火斥候制度,遇有敵情,則可以迅速得到情報。但由于遼興宗過于輕敵,以為短期内即可克敵制勝,部隊隻帶足五個月的糧草,但五個月之後,仍未完全平息塔裡幹之叛,遼朝軍隊糧草奇缺,大多叛逃回國,行軍都監蕭污魯因調運糧草不濟而被罷免。耶律仁先采用安撫與軍事進攻相輔相成的手段,占領阻蔔部的軍事要沖,遼軍迅速擊敗了阻蔔塔裡幹部落的叛軍。
但塔裡幹仍不死心,糾集其殘餘勢力前來進攻遼軍,耶律仁先派兵予以迎頭痛擊,再一次擊敗塔裡幹叛軍。後來,塔裡幹聯合阻蔔部的把裡斯和秃沒二酋長,準備與遼軍決一雌雄,把裡斯等人率本部人馬到前線增援塔裡幹,但他們了解到塔裡幹屢戰屢敗,遼軍攻勢越來越猛的情況後,懾于遼軍的強大勢力,把裡斯和秃沒二酋長不戰而降。經過九個月的浴血苦戰,遼軍取得了平叛的勝利。遼軍将投降遼朝的阻蔔部酋長全部押解到京師。
阿雲之獄
熙甯元年(1068)正月,登州(今山東蓬萊)婦女阿雲母親去逝後,守喪時間尚未結束,便嫁給當地農民韋阿大。但阿雲嫌韋阿大其貌不揚、醜陋不堪,準備趁夜用刀殺死韋阿大,韋阿大受傷十餘處,被砍去一截手指,但韋阿大并未喪生,阿雲作案後向司法機關投案自首。
案件上報審刑院和大理寺後,審刑院和大理寺認為應該按照違反法令結婚的敕令判決這一案件,免除阿雲的死刑。而登州知州許遵則認為應該按照國家的有關法律條文來審理此案,雙方争執不下,于是将這一案件移交刑部,刑部也同意大理寺和審刑院的意見。但許遵認為用敕令條文加以判決很不合理,于是上書宋神宗,宋神宗下令翰林學士和知制诰出面審理此案。
翰林學士王安石和知制诰司馬光開始對案情進行分析,王安石認為許遵的判決是合理的,而司馬光則認為審刑院和刑部的判決是正确的,其後禦史中丞滕甫、侍禦史錢颉等人上書支持司馬光的意見。王安石執政後,為阿雲之獄專門修改了法律條文。熙甯二年(1069)八月,呂公着上書支持王安石的意見。
于是審刑院、大理寺官員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等人上書反駁呂公着。禦史中丞呂誨等禦史台官員,文彥博等人也上書認為謀殺案不應該考慮坦白自首因素。其後,知雜禦史劉述、集賢校理丁諷、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等人都因不懂法而執法被彈劾,司馬光上書朝廷,竭力為這些官員辯解,才使他們免罷。
韓琦築甘谷城
韓琦派遣李立之到開封府(今河南開封)請求修築甘谷城(今甘肅通渭南)。樞密院官僚認為甘谷城地處秦州(今甘肅天水)熟戶(歸順于宋朝的少數民族)領地之上,假如朝廷在此修築城,今後還得有相應的配套軍事工程,使甘谷城與渭州(今甘肅平涼)連接起來,同時,宋朝還必須添屯大量兵馬,政府很難供給糧饷等等。
因而朝廷沒有采納韓琦的建議。李立之回到陝西後,韓琦再一次上書朝廷,堅持要求修築甘谷城。他認為目前西夏所占有的地區與古代匈奴所占據的領土相差無幾,宋朝從前放棄了靈州(今甯夏青銅峽東),便失去了砍斷西夏“臂膀”的有利條件。如果在甘谷城修築城堡,可以連通雞川(今甘肅通渭東南)、古渭等城,形成一個防禦西夏的強大體系,并可以阻止西夏吞并古渭寨一帶蕃部的企圖,可以防止蓍部部落如木征、瞎藥、青唐等聯合起來反抗宋朝。
因而修築甘谷城是一舉三得的事情。熙甯元年(1068)二月宋神宗采納了韓琦的建議。韓命令秦鳳路副都總管楊文廣(宋初名将楊業之孫)前往修築甘谷城。韓琦還建議朝廷在秦鳳路擦珠谷一帶修一大城堡,修成之後,宋神宗賜名為通渭(甘肅隴西縣東),這樣就将古渭寨與甘谷城連接起來了。
王安石與司馬光論理财
王安石與司馬光在如何理财問題上發生了根本分歧。王安石認為宋代“積貧”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财政支出過多,而在于生産甚少,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這篇萬言書裡詳細闡述了自己的論點。他認為理财的最好辦法就是廣開财源,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費",從而扭轉政府财政虧空的局面。
而司馬光在嘉祐七年(1062)的《論理财疏》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财方針,他認為自然界所能生産的物質财富一般都保持在一定的數量上,隻會因為水旱等自然災害而增産或減産。而政府财政支出過多,冗兵、冗官、冗費等是造成國家财政緊張的直接原因。因而司馬光的理财方針是節流,即節省一切不必要的财政開支。這樣就能解決國家财政危機問題。
熙甯元年(1068)九月,王安石與司馬光同時被任命為翰林學士時,司馬光、王矽,王安石三人将《郊赉劄子》遞呈給宋神宗,其中談到郊祀之禮時賞賜過濫,耗去了政府大量财産。于是關于理财問題,王安石、司馬光二人又發生了一場争論。司馬光說:目前國家财政緊張,自然災害頻仍,政府應節省一切不必要的開支(冗費),而節省冗費應該從皇帝身邊的親貴、權臣開始。
王安石回答說:本朝版圖遼闊,皇帝在郊祀之禮時賞賜大臣點兒東西算不了什麼,節約這一筆開支也未必能使國家财政富裕起來,況且理财并非當務之急。司馬光又說:本朝從宋真宗未年以來财政發生危機,國用不足,近年以來,财政虧空局面越來越嚴重,節省冗費難道不是當務之急嗎?
王安石反駁說:國家财政支出不足,主要原因在于沒有一個善于理财的大臣。司馬光針鋒相對道:善于理财的大臣不過是千方百計地搜刮老百姓的錢财,這樣全國人民隻會越來越窮,從而被迫流離失所,然後起而為盜賊,這對國家難道是有利的嗎?王安石回答說:這種人并不是善于理财之人,善于理财者應該不增加老百姓負擔而使國家财政日益富裕。司馬光說:這是漢代桑弘羊欺騙漢武帝的說法,純屬欺人之談,況且天
地所産的财富有一定的數額,這些财富不是儲藏在民間,便是儲藏在國家的倉庫之中,果真如桑弘羊所說,那麼漢武帝末年盜賊公行的現象又當作何解釋呢?難道不是老百姓窮困不堪而起而為盜嗎?這次争論後不久,王安石升任參知政事,設置制置三司條例司機構,開始了變法運動。
變法派所實施的一切措施都遭到了以司馬光為首的一些官僚的反對,司馬光還接二連三地寫信給王安石,大談孔孟之道,攻擊王安石大談理财之事,違背了孔孟之道。王安石對司馬光的诘難進行了有力的反駁,這就是有名的《答司馬谏議書》。上述即是王安石與司馬光在理财問題上的重大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