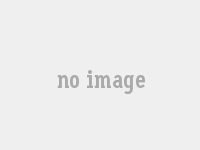個人設定
籍貫:東京(今河南開封)。
屬國:宋朝,楚國(王慶所建)。
身份:楚王。
家庭:王家。
父親:王砉。
後妃:段三娘。
國丈:段太公。
國舅:段二、段五。
表親:範全。
原配:牛氏。
出自:簡本《水浒傳》,120回本《水浒全傳》。
登場回目:(120回本)第101回謀墳地陰險産逆蹈春陽妖豔生奸。
創作原型:王則(北宋時河北士兵起義領袖)。
家世
王慶原來是東京開封府内一個副排軍。他父親王砉,是東京大富戶,專一打點衙門,唆結訟,放刁把濫,排陷良善,因此人都讓他些個。他聽信了一個風水先生,看中了一塊陰地,當出大貴之子。這塊地,就是王砉親戚人家葬過的,王砉與風水先生設計陷害。王砉出尖,把那家告紙謊狀,官司累年,家産蕩盡,那家敵王砉不過,離了東京,遠方居住。
生平後來王慶造反,三族皆夷,獨此家在遠方,官府查出是王砉被害,獨得保全。王砉奪了那塊墳地,葬過父母,妻子懷孕彌月。王砉夢虎入室,蹲踞堂西,忽被獅獸突入,将虎銜去。王砉覺來,老婆便産王慶。那王慶從小浮浪,到十六七歲,生得身雄力大,不去讀書,專好鬥瞈走馬,使輪棒。那王砉夫妻兩口兒,單單養得王慶一個,十分愛恤,自來護短,憑他慣了,到得長大,如何拘管得下。王慶賭的是錢兒,宿的是娼兒,喝的是酒兒。
王砉夫婦,也有時訓誨他。王慶逆性發作,将父母詈罵,王砉無可奈何,隻索由他。過了六七年,把個家産費得罄盡,單靠着一身本事,在本府充做個副排軍。一有錢鈔在手,三兄四弟,終日大酒大肉價同;若是有些不如意時節,拽出拳頭便打,所以衆人又懼怕他,又喜歡他。
風流情史
王慶獨自閑耍了一回,向那圃中一顆傍池的垂楊上,将肩胛斜倚着,欲等個相識到來,同去酒肆中吃三杯進城。無移時,隻見池北邊十來個幹辦、虞候、伴當、養娘人等,簇着一乘轎子,轎子裡面如花似朵的一個年少女子。那女子要看景緻,不用竹簾。那王慶好的是女色,見了這般标緻的女子,把個魂靈都吊下來,認得那夥幹辦、虞候是樞密童貫府中人。當下王慶遠遠地跟着轎子,随了那夥人來到艮嶽。那艮嶽在京城東北隅,即道君皇帝所築,奇峰怪石,古木珍禽,亭榭池館,不可勝數。外面朱垣绯戶,如禁門一般,有内相禁軍看守,等閑人腳指頭兒也不敢踅到門前。那簇人歇下轎,養娘扶女子出了轎,迳望艮嶽門内,袅袅娜娜,妖妖娆娆走進去。那看門禁軍内侍,都讓開條路,讓他走進去了。
原來那女子是童貫之弟童贳之女,楊戬的外孫。童貫撫養為己女,許配蔡攸之子,卻是蔡京的孫兒媳婦了,小名叫做嬌秀,年方二八。他禀過童貫,乘天子兩日在李師師家娛樂,欲到艮嶽遊玩。
王慶再踅到艮嶽前,又停了一回,隻見那女子同了養娘,輕移蓮步,走出艮嶽來,且不上轎,看那良嶽外面的景緻。王慶踅上前去看那女子時,真個标緻。有混江龍詞為證:豐資毓秀,那裡個金屋堪收?點櫻桃小口,橫秋水雙眸。若不是昨夜晴開新月皎,怎能得今朝腸斷小梁州。芳芬綽約蕙蘭俦,香飄雅麗芙蓉袖,兩下裡心猿都被月引花鈎。
王慶看到好處,不覺心頭撞鹿,骨軟筋麻,好便似雪獅子向火,霎時間酥了半邊。那嬌秀在人叢裡,見王慶的相貌:鳳眼濃眉如畫,微須白面紅顔。頂平額闊滿天倉,七尺身材壯健。善會偷香竊玉,慣的賣俏行奸。凝眸呆想立人前,俊俏風流無限。
那嬌秀一眼着王慶風流,也看上了他。當有幹辦、虞候喝開衆人,養娘扶嬌秀上轎,衆人簇擁着,轉東過西,卻到酸棗門外嶽廟裡來燒香。王慶又跟随到嶽廟裡,人山人海的,挨擠不開,衆人見是童樞密處虞候、幹辦,都讓開條路。那嬌秀下轎進香,王慶挨踅上前,卻是不能近身,又恐随從人等叱,假意與廟祝厮熟,幫他點燭燒香,一雙眼不住的溜那嬌秀,嬌秀也把眼來頻。原來蔡攸的兒子,生來是憨呆的。那嬌秀在家,聽得幾次媒婆傳說是真,日夜叫屈怨恨。
今日見了王慶風流俊俏,那小鬼頭兒春心也動了。當下童府中一個董虞候,早已瞧科,認得排軍王慶。董虞候把王慶劈臉一掌打去,喝道:“這個是什麼人家的宅眷!你是開封府一個軍健,你好大膽,如何也在這裡挨挨擠擠。待俺對相公說了,教你這顆驢頭,安不牢在頸上!”王慶那敢則聲,抱頭鼠竄,奔出廟門來,噀一口唾,叫聲道:“碎!我直恁這般呆!癞蝦蟆怎想吃天鵝肉!”當晚忍氣吞聲,慚愧回家。誰知那嬌秀回府,倒是日夜思想,厚賄侍婢,反去問那董虞候,教他說王慶的詳細。侍婢與一個薛婆子相熟,同他做了馬泊六,悄地勾引王慶從後門進來,人不知、鬼不覺,與嬌秀勾搭。王慶那厮,喜出望外,終日飲酒。
光陰荏苒,過了三月,正是樂極生悲,王慶一日吃得爛醉如泥,在本府正排軍張斌面前露出馬腳,遂将此事彰揚開去,不免吹在童貫耳朵裡。童貫大怒,思想要尋罪過擺撥他,不在話下。且說王慶因此事發覺,不敢再進童府去了。
刺配陝州
兩個公人扶着王慶進了開封府,府尹正坐在堂中虎皮交椅上。兩個公人帶王慶上前禀道:“奉老爺鈞旨,王慶拿到。”王慶勉強朝上磕了四個頭。府尹喝道:“王慶,你是個軍健,如何怠玩,不來伺候?”王慶又把那見怪閃肭的事,細禀一遍道:“實是腰肋疼痛,坐卧不甯,行走不動,非敢怠玩。望相公方便。”府尹聽罷,又見王慶臉紅,大怒喝道:“你這厮專一酗酒為非,幹那不公不法的事,今日又捏妖言,欺诳上官!”喝教扯下去打。王慶那裡分說得開?當下把王慶打得皮開肉綻,要他招認捏造妖書,煽惑愚民,謀為不軌的罪。王慶昨夜被老婆克剝,今日被官府拷打,真是雙斧伐木,死去再醒,吃打不過,隻得屈招。府尹錄了王慶口詞,叫禁子把王慶将刑具枷扭來釘了,押下死囚牢裡,要問他個捏造妖書,謀為不軌的死罪。禁子将王慶扛打擡入牢去了。
原來童貫密使人分付了府尹,正要尋罪過擺撥他,可可的撞出這節怪事來。那時府中上下人等,誰不知道嬌秀這件勾當,都紛紛揚揚的說開去:“王慶為這節事得罪,如今一定不能個活了。”那時蔡京、蔡攸耳朵裡頗覺不好聽,父子商議,若将王慶性命結果,此事愈真,醜聲一發播傳。于是密挽心腹官員,與府尹相知的,教他速将王慶刺配遠惡軍州,以滅其迹。蔡京、蔡攸擇日迎娶嬌秀成親,一來遮掩了童貫之羞,二來滅了衆人議論。蔡攸之子,左右是呆的,也不知嬌秀是處子不是處子,這也不在話下。
且說開封府尹遵奉蔡太師處心腹密話,随即升廳。那日正是辛酉日,叫牢中提出王慶,除了長枷,斷了二十脊杖,喚個文筆匠刺了面頰,量地方遠近,該配西京管下陝州牢城。當廳打一面十斤半團頭鐵葉護身枷釘了,貼上封皮,押了一道牒文,差兩個防送公人,叫做孫琳、賀吉,監押前去。
三人出開封府來,隻見王慶的丈人牛大戶接着,同王慶、孫琳、賀吉到衙前南街酒店裡坐定。牛大戶叫酒保搬取酒肉,吃了三杯兩盞,牛大戶向身邊取出一包散碎銀兩,遞與王慶道:“白銀三十兩,把與你路途中使用。”王慶用手去接道:“生受泰山!”牛大戶推着王慶的手道:“這等容易!我等閑也不把銀兩與你,你如今配去陝州,一千餘裡,路遠山遙,知道你幾時回來?你調戲了别人家女兒,卻不耽誤了自己的妻子!老婆誰人替你養?又無一男半女,田地家産可以守你。你須立紙休書,自你去後,任從改嫁,日後并無争執。如此,方把銀子與你。”王慶平日會花費,思想:“我囊中又無十兩半斤銀兩,這陝西如何去得?”左思右算,要那銀兩使用,歎了兩口氣道:“罷,罷!隻得寫紙休書。”牛大戶一手接紙,一手交銀,自回去了。
王慶同了兩個公人到家中來收拾行囊包裹,老婆已被牛大戶接到家中去了,把個門兒鎖着。王慶向鄰舍人家借了斧鑿,打開門戶,到裡面看時,凡老婆身上穿着的,頭上插戴的,都将去了。王慶又惱怒,又凄慘。央間壁一個周老婆子,到家備了些酒食,把與公人吃了,将銀十兩送與孫琳、賀吉道:“小人棒瘡疼痛,行走不動,欲将息幾日,方好上路。”孫琳、賀吉得了錢,也是應允,怎奈蔡攸處挽心腹催促公人起身。王慶将家夥什物胡亂變賣了,交還了胡員外家賃房。
此時王慶的父王砉,已被兒子氣瞎了兩眼,另居一處,兒子上門,不打便罵。今日聞得兒子遭官司刺配,不覺心痛,教個小厮扶着,走到王慶屋裡,叫道:“兒了呀,你不聽我的訓誨,以緻如此。”說罷,那雙盲昏眼内,吊下淚來。王慶從小不曾叫王砉一聲爺的,今值此家破人離的時節,心中也酸楚起來,叫聲道:“爺,兒子今日遭恁般屈官司,叵耐牛老兒無禮,逼我寫了休妻的狀兒,才把銀子與我。”王砉道:“你平日是愛妻子,孝丈人的,今日他如何這等待你?”王慶聽了這兩句搶白的話,便氣憤憤的不來睬着爺,徑同兩個公人,收拾出城去了。王砉頓足搥胸道:“是我不該來看那逆種!”複扶了小厮自回,不題。
邙東結仇
卻說王慶同了孫琳、賀吉離了東京,賃個僻靜所在,調治十餘日,棒瘡稍愈,公人催促上路,迤逦而行,望陝州投奔。此時正是六月初旬,天氣炎熱,一日止行得四五十裡,在路上免不得睡死人床,吃不滾湯。三個人行了十五六日,過了嵩山。一日正在行走,孫琳用手向西指着遠遠的山峰說道:“這座山叫做北邙山,屬西京管下。”三人說着話,趁早涼,行了二十餘裡。望見北邙山東,有個市鎮,隻見四面村農,紛紛的投市中去。那市東人家稀少處,丁字兒列着三株大柏樹。樹下陰陰,隻見一簇人亞肩叠背的圍着一個漢子,赤着上身,在那陰涼樹下吆吆喝喝地使棒。三人走到樹下歇涼。王慶走得汗雨淋漓,滿身蒸濕,帶着護身枷,挨入人叢中,掂起腳看那漢使捧。
看了一歇兒,王慶不覺失口笑道:“那漢子使的是花棒。”那漢正使到熱鬧處,聽了這句話,收了棒看時,卻是個配軍。那漢大怒,便罵:“賊配軍,俺的鎗棒遠近聞名,你敢開了那鳥口,輕慢我的棒,放出這個屁來!”丢下棒,提起拳頭,劈臉就打。隻見人叢中走出兩個少年漢子來攔住道:“休要動手!”便問王慶道:“足下必是高手。”王慶道:“亂道這一句,惹了那漢子的怒。小人鎗棒也略曉得些兒。”那邊使棒的漢子怒罵道:“賊配軍,你敢與我比試罷?”那兩個人對王慶道:“你敢與那漢子使合棒,若赢了他,便将這掠下的兩貫錢都送與你。”王慶笑道:“這也使得。”分開衆人,向賀吉取了杆棒,脫了汗衫,拽紮起裙子,掣棒在手。衆人都道:“你項上帶着個枷兒,卻如何輪棒?”王慶道:“隻這節兒稀罕。帶着行枷赢了他,才算手段。”
衆人齊聲道:“你若帶枷赢了,這兩貫錢一定與你。”便讓開路,放王慶入去。那使棒的漢也掣棒在手,使個旗鼓,喝道:“來,來,來!”王慶道:“列位恩官,休要笑話。”那邊漢子明欺王慶有護身枷礙着,吐個門戶,喚做“蟒蛇吞象勢”。王慶也吐個勢,喚做“蜻蜓點水勢”。那漢喝一聲,便使棒蓋将入來。王慶望後一退,那漢趕入一步,提起棒,向王慶頂門又複一棒打下來。王慶将身向左一閃,那漢的棒打個空,收棒不叠。王慶就那一閃裡,向那漢右手一棒劈去,正打着右手腕,把這條棒打落下來。幸得棒下留情,不然把個手腕打斷。
衆人大笑。王慶上前執着那漢的手道:“沖撞休怪!”那漢右手疼痛,便将左手去取那兩貫錢。衆人一齊嚷将起來道:“那厮本事低醜,适才講過,這錢應是赢棒的拿!”隻見在先出尖上前的兩個漢子,劈手奪了那漢兩貫錢,把與王慶道:“足下到敝莊一叙。”那使棒的拗衆人不過,隻得收拾了行仗,望鎮上去了。衆人都散。
兩個漢子邀了王慶,同兩個公人,都戴個涼笠子,望南抹過兩三座林子,轉到一個村坊。林子裡有所大莊院,一周遭都是土牆,牆處有二三百株大柳樹。莊外新蟬噪柳,莊内乳燕啼梁。兩個漢子,邀王慶等三人進了莊院,入到草堂,叙禮罷,各人脫下汗衫麻鞋,分賓主坐下。莊主問道:“列位都象東京口氣。”王慶道了姓名,并說被府尹陷害的事。說罷,請問二位高姓大名。二人大喜。那上面坐的說道:“小可姓龔,單名個端字,這個是舍弟,單名個正字。舍下祖居在此,因此,這裡叫做龔家村。這裡屬西京新安縣管下。”說罷,叫莊客替三位澣濯那濕透的汗衫,先汲涼水來解了暑渴,引三人到上房中洗了澡,草堂内擺上桌子,先吃了現成點心,然後殺雞宰鴨,煮豆摘桃的置酒管待。
莊客重新擺設,先搬出一碟剝光的蒜頭,一碟切斷的壯蔥,然後搬出菜蔬、果品、魚肉、雞鴨之類。龔端請王慶上面坐了,兩個公人一代兒坐下,龔端和兄弟在下面備席,莊客篩酒。王慶稱謝道:“小人是個犯罪囚人,感蒙二位錯愛,無端相擾,卻是不當。”龔端道:“說那裡話!誰人保得沒事?那個帶着酒食走的?”當下猜枚行令,酒至半酣,龔端開口道:“這個敝村,前後左右,也有二百餘家,都推愚弟兄做個主兒。小可弟兄兩個,也好使些拳棒,壓服衆人。
今春二月,東村賽神會,搭台演戲,小可弟兄到那邊耍子,與彼村一個人,喚做黃達,因賭錢鬥口,被那厮痛打一頓,俺弟兄兩個,也赢不得他。黃達那厮,在人面前誇口稱強,俺兩個奈何不得他,隻得忍氣吞聲。适才見都排棒法十分整密,俺二人願拜都排為師父,求師父點撥愚弟兄,必當重重酬謝。”王慶聽罷大喜,謙讓了一回。龔端同弟随即拜王慶為師。當晚直飲至盡醉方休,乘涼歇息。
管營刁難
不覺的過了兩個月,時遂秋深天氣。忽一日,王慶正在單身房裡閑坐,隻見一個軍漢走來說道:“管營相公喚你。”王慶随了軍漢,來到點視廳上磕了頭。管營張世開說道:“你來這裡許多時,不曾差遣你做甚麼。我要買一張陳州來的好角弓;那陳州是東京管下,你是東京人,必知價值真假。”說罷,便向袖中摸出一個紙包兒,親手遞與王慶道:“紋銀二兩,你去買了來回話。”王慶道:“小的理會得。”接了銀子,來到單身房裡,拆開紙包,看那銀子,果是雪丢,将等子稱時,反重三四分。王慶出了本營,到府北街市上弓箭鋪中,止用得一兩七錢銀子,買了一張真陳州角弓;将回來,張管營已不在廳上了。
王慶将弓交與内宅親随伴當送進去,喜得落了他三錢銀子。明日張世開又喚王慶到點視廳上說道:“你卻幹得事來,昨日買的角弓甚好。”王慶道:“相公須教把火來放在弓廂裡,不住的焙,方好。”張世開道:“這個曉得。”從此張世開日日差王慶買辦食用供應,卻是不比前日發出現銀來,給了一本帳簿,教王慶将日逐買的,都登記在簿上。那行鋪人家,那個肯賒半文?王慶隻得取出己财,買了送進衙門内去。張世開嫌好道歉,非打即罵。及至過了十日,将簿呈遞,禀支價銀,那裡有毫忽兒發出來。如是月餘,被張管營或五棒,或十棒,或二十,或三十,前前後後,總計打了三百餘棒,将兩腿都打爛了;把龔端送的五十兩銀子,賠費得罄盡。
一日,王慶到營西武功牌坊東側首,一個修合丸散,賣飲片,兼内外科,撮熟藥,又賣杖瘡膏藥的張醫士鋪裡,買了幾張膏藥,貼療杖瘡。張醫士一頭與王慶貼膏藥,一頭口裡說道:“張管營的舅爺,龐大郎,前日也在這裡取膏藥,貼治右手腕。他說在邙東鎮上跌壞的,咱看他手腕,像個打壞的。”王慶聽了這句話,忙問道:“小人在營中,如何從不曾見面?”張醫士道:“他是張管營小夫人的同胞兄弟,單諱個元字兒。那龐夫人是張管營最得意的。那龐大郎好的是賭錢,又要使槍棒耍子。
虧了這個姐姐,常照顧他。”王慶聽了這一段話,九分猜是前日在柏樹下被俺打的那厮,一定是龐元了;怪道張世開尋罪過擺布俺。王慶别了張醫士,回到營中,密地與管營的一個親随小厮,買酒買肉的請他,又把錢與他,慢慢的密問龐元詳細。那小厮的說話,與前面張醫士一般,更有兩句備細的話,說道:“那龐元前日在邙東鎮上被你打壞了,常在管營相公面前恨你。你的毒棒,隻恐兀是不能免哩!”正是:
好勝誇強是禍胎,謙和守分自無災。
隻因一棒成仇隙,如今加利奉還來。
殺人出逃
那王慶從小惡逆,生身父母,也再不來觸犯他的。當下逆性一起,道是“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一不做,二不休,挨到更餘,營中人及衆囚徒都睡了,悄地踅到内宅後邊,爬過牆去,輕輕的拔了後門的栓兒,藏過一邊。那星光之下,照見牆垣内東邊有個馬廄,西邊小小一間屋,看時,乃是個坑廁。王慶掇那馬廄裡一扇木栅,豎在二重門的牆邊,從木栅爬上牆去,從牆上抽起木栅,豎在裡面,輕輕溜将下去。先拔了二重門栓,藏過木栅;裡面又是牆垣,隻聽得牆裡邊笑語喧嘩。
王慶踅到牆邊,伏着側耳細聽,認得是張世開的聲音,一個婦人聲音,又是一個男子聲音,卻在那裡喝酒閑話。王慶竊聽多時,忽聽得張世開說道:“舅子,那厮明日來回話,那條性命,隻在棒下。”又聽得那個男子說道:“我算那厮身邊東西,也七八分了。姐夫須決意與我下手,出這口鳥氣!”張世開答道:“隻在明後日教你快活罷了!”那婦人道:“也夠了!你每索罷休!”那男子道:“姐姐說那裡話?你莫管!”王慶在牆外聽他每三個一遞一句,說得明白,心中大怒,那一把無明業火,高舉三千丈,按納不住,恨不得有金剛般神力,推倒那粉牆,搶進去殺了那厮每。正是:
爽口物多終作病,快心事過必為殃。
金風未動蟬先覺,無常暗送怎提防!
當下王慶正在按納不住,隻聽得張世開高叫道:“小厮,點燈照我往後面去登東廁。”王慶聽了這句,連忙掣出那把解手尖刀,将身一堆兒蹲在那株梅樹後,隻聽得呀的一聲,那裡面兩扇門兒開了。王慶在黑地裡觀看卻是日逐透遞消息的那個小厮,提個行燈,後面張世開擺将出來。不知暗裡有人,望着前,隻顧走,到了那二重門邊,罵道:“那些奴才每,一個也不小心,如何這早晚不将這栓兒拴了?”那小厮開了門,照張世開方才出得二重門,王慶悄悄的挨将上來。張世開聽得後面腳步響,回轉頭來,隻見王慶右手掣刀,左手叉開五指,搶上前來。張世開把那心肝五髒,都提在九霄雲外,叫聲道:“有賊!”說時遲,那時快,被王慶早落一刀,把張世開齊耳根連脖子砍着,撲地便倒。
那小厮雖是平日與王慶厮熟,今日見王慶拿了明晃晃一把刀,在那裡行兇,怎的不怕?卻待要走,兩隻腳一似釘住了的;再要叫時,口裡又似啞了的,喊不出來,端的驚得呆了。張世開正在掙命,王慶趕上,照後心又刺一刀,結果了性命。龐元正在姐姐房中吃酒,聽得外面隐隐的聲喚,點燈不叠,急跑出來看視。王慶見裡面有人出來,把那提燈的小厮隻一腳,那小厮連身帶燈跌去,燈火也滅了。龐元隻道張世開打小厮,他便叫道:“姐夫,如何打那小厮?”卻待上前來勸,被王慶飛搶上前,暗地裡望着龐元一刀刺去,正中脅肋;龐元殺豬也似喊了一聲,攧翻在地。
王慶揪住了頭發,一刀割下頭來。龐氏聽得外面喊聲兇險,急叫丫嬛點燈,一同出來照看。王慶看見龐氏出來,也要上前來殺。你道有恁般怪事!說也不信。王慶那時轉眼間,便見龐氏背後有十數個親随伴當,都執器械,趕喊出來。王慶慌了手腳,搶出外去,開了後門,越過營中後牆,脫下血污衣服,揩淨解手刀,藏在身邊。聽得更鼓,已是三更,王慶乘那街坊人靜,踅到城邊。那陝州是座土城,城垣不甚高,濠塹不甚深,當夜被王慶越城去了。
且不說王慶越城,再說張世開的妾龐氏,隻同得兩個丫嬛,點燈出來照看,原無甚麼伴當同他出來。他先看見了兄弟龐元血渌渌的頭在一邊,體在一邊,唬得龐氏與丫嬛都面面相觑,正如分開八片頂陽骨,傾下半桶冰雪水,半晌價說不出話。當下龐氏三個,連跌帶滾,戰戰兢兢的跑進去,聲張起來,叫起裡面親随,外面當值的軍牢,打着火把,執着器械,都到後面照看。隻見二重門外,又殺死張管營,那小厮跌倒在地,尚在掙命,口中吐血,眼見得不能夠活了。衆人見後門開了,都道是賊在後面來的,一擁到門外照看,火光下照見兩疋彩段,抛在地下,衆人齊聲道是王慶。連忙查點各囚徒,隻有王慶不在。
當下鬧動了一營,及左右前後鄰舍衆人,在營後牆外,照着血污衣服,細細簡認,件件都是王慶的。衆人都商議,趁着未開城門,去報知州尹,急差人搜捉。此時已是五更時分了。州尹聞報大驚,火速差縣尉簡驗殺死人數,及行兇人出沒去處;一面差人教将陝州四門閉緊,點起軍兵,并緝捕人員,城中坊廂裡正,逐一排門搜捉兇人王慶。閉門鬧了兩日,家至戶到,逐一挨查,并無影迹。州尹押了文書,委官下該管地方各處鄉保都村,排家搜捉,緝捕兇首。寫了王慶鄉貫,年甲,貌相,模樣,畫影圖形,出一千貫信賞錢。如有人知得王慶下落,赴州告報,随文給賞;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食宿者,事發到官,與犯人同罪。遍行鄰近州縣,一同緝捕。
巧遇範全
且說王慶當夜越出陝州城,抓紮起衣服,從城濠淺處,去過對岸,心中思想道:“雖是逃脫了性命,卻往那裡去躲避好?”此時是仲冬将近,葉落草枯,星光下看得出路徑。王慶當夜轉過了三四條小路,方才有條大路。急忙忙的奔走,到紅日東升,約行了六七十裡,卻是望着南方行走,望見前有人家稠密去處。王慶思想身邊尚有一貫錢,且到那裡買些酒食吃了,再算計投那裡去。不多時,走到市裡,天氣尚早,酒肉店尚未開哩。隻有朝東一家屋檐下,挂個安歇客商的破燈籠兒,是那家昨晚不曾收得,門兒兀是半開半掩。王慶上前,呀的一聲推進門去,隻見一個人兀未梳洗,從裡面走将出來。
王慶看時,認得這個乃是我母姨表兄院長範全。他從小随父親在房州經紀得利,因此就充做本州島兩院押牢節級。今春三月中,到東京公幹,也在我家住過幾日”。當下王慶叫道:“哥哥别來無恙!”範全也道:“是像王慶兄弟。”見他這般模樣,臉上又刺了兩行金印,正在疑慮,未及回答。那邊王慶見左右無人,托地跪下道:“哥哥救兄弟則個!”範全慌忙扶起道:“你果是王慶兄弟麼?”王慶搖手道:“禁聲!”範全會意,一把挽住王慶袖子,扯他到客房中,卻好範全昨晚揀賃的是獨宿房兒。範全悄地忙問:“兄弟何故如此模樣?”王慶附耳低言的,将那吃官司刺配陝州的事,述了一遍。次後說張世開報仇忒狠毒,昨夜已是如此如此。
範全聽罷大驚,躊躇了一回,急急的梳洗吃飯,算還了房錢飯錢,商議教王慶隻做軍牢跟随的人,離了飯店,投奔房州來。王慶于路上問範全為何到此,範全說道:“蒙本處州尹,差往陝州州尹處投遞書劄,昨日方讨得回書,随即離了陝州,因天晚在此歇宿;卻不知兄弟正在陝州,又做出恁般的事來。”範全同了王慶,夜止曉行,潛逃到房州。才過得兩日,陝州行文挨捕兇人王慶。範全捏了兩把汗,回家與王慶說知:“城中必不可安身。城外定山堡東,我有幾間草房,又有二十餘畝田地,是前年買下的。如今發幾個莊客在那裡耕種,我兄弟到那裡躲避幾日,卻再算計。”
範全到黑夜裡,引王慶出城,到定山堡東,草房内藏匿;卻把王慶改姓改名,叫做李德。範全思想王慶臉上金印不穩;幸得昔年到建康,聞得“神醫”安道全的名,用厚币交結他,學得個療金印的法兒,卻将毒藥與王慶點去了,後用好藥調治,起了紅疤,再将金玉細末,塗搽調治,二月有餘,那疤痕也消磨了。
結識段三娘
當下王慶閑看了一回,看得技養,見那戲台裡邊,人叢裡,有個彪形大漢兩手靠着桌子,在杌子上坐地。那漢生的圓眼大臉,闊肩細腰,桌上堆着五貫錢,一個色盆,六隻骰子,卻無主顧與他賭。王慶思想道:“俺自從吃官司到今日,有十數個月,不曾弄這個道兒了。前日範全哥哥把與我買柴薪的一錠銀在此,将來做個梢兒,與那厮擲幾擲,赢幾貫錢回去買果兒吃。”當下王慶取出銀子,望桌上一丢,對那漢道:“胡亂擲一回。”那漢一眼瞅着王慶說道:“要擲便來。”說還未畢,早有一個人,向那前面桌子邊人叢裡挨出來,貌相長大,與那坐下的大漢,仿佛相似。對王慶說道:“秃秃,他這錠銀怎好出主?将銀來,我有錢在此。你赢了,每貫隻要加利二十文。”王慶道:“最好!”與那人打了兩貫錢,那人已是每貫先除去二十文。
王慶道:“也罷!”随即與那漢講過擲朱窩兒。方擲得兩三盆,随有一人挨下來,出主等擲。那王慶是東京積賭慣家,他信得盆口真,又會躲閃打浪,又狡猾奸詐,下捵主作弊;那放囊的,乘鬧裡踅過那邊桌上去了,那挨下來的,說王慶擲得兇,收了去,隻替那漢拈頭兒。王慶一口氣擲赢了兩貫錢,得了采,越擲得出,三紅四聚,隻管撒出來。那漢性急反本,擲下便是絕塌腳小四不脫手。王慶擲了九點,那漢偏調出倒八來無一個時辰,把五貫錢輸個罄盡。王慶赢了錢,用繩穿過兩貫,放在一邊,待尋那漢贖梢,又将那三貫穿縛停當。方欲将肩來負錢,那輸的漢子喝道:“你待将錢往那裡去?隻怕是才出爐的,熱的熬炙了手。”
王慶怒道:“你輸與我的,卻放那鳥屁?”那漢睜圓怪眼罵道:“狗弟子孩兒,你敢傷你老爺!”王慶罵道:“村撮鳥,俺便怕你把拳打在俺肚裡拔不出來,不将錢去!”那漢提起雙拳,望王慶劈臉打來。王慶側身一閃,就勢接住那漢的手,将右肘向那漢胸脯隻一搪,右腳應手,将那漢左腳一勾。那漢是蠻力,那裡解得這跌法,撲通的望後攧翻,面孔朝天,背脊着地。那立攏來看的人,都笑起來。那漢卻待掙紮,被王慶上前按住,照實落處隻顧打。
那在先放囊的走來,也不解勸,也不幫助,隻将桌上的錢都搶去了。王慶大怒,棄了地上漢子,大踏步趕去。隻見人叢裡閃出一個女子來,大喝道:“那厮不得無禮!有我在此!”王慶看那女子,生的如何:眼大露兇光,眉粗麤橫殺氣。腰肢坌蠢,全無袅娜風情;面皮頑厚,惟賴粉脂鋪翳。異樣钗镮插一頭,時興馴镯露雙臂。頻搬石臼,笑他人氣喘急促;常掇井欄,誇自己膂力不費。針線不知如何拈,拽腿牽拳是長技。
那女子有二十四五年紀;他脫了外面衫子,卷做一團,丢在一個桌上,裡面是箭杆小袖緊身,鹦哥綠短襖,下穿一條大檔紫夾?褲兒,踏步上前,提起拳頭,望王慶打來。王慶見他是女子,又見他起拳便有破綻,有意耍他,故意不用快跌,也拽雙拳吐個門戶,擺開解數,與那女子相撲。但見:拽開大四平,踢起雙飛腳。仙人指路,老子騎鶴。拗鸾肘出近前心,當頭炮勢侵額角。翹跟淬地龍,扭腕擎天橐。這邊女子,使個蓋頂撒花;這裡男兒,耍個遶腰貫索。兩個似迎風貼扇兒,無移時急雨催花落。
那時粉頭已上台做笑樂院本,衆人見這邊男女相撲,一齊走攏來,把兩人圍在圈子中看。那女子見王慶隻辦得架隔遮攔,沒本事鑽進來,他便觑個空,使個“黑虎偷心勢”,一拳望王慶劈心打來。王慶将身一側,那女子打個空,收拳不叠。被王慶就勢扭捽定,隻一交,把女子攧翻;剛剛着地,順手兒又抱起來。這個勢:叫做“虎抱頭”。王慶道:“莫污了衣服。休怪俺沖撞,你自來尋俺。”那女子毫無羞怒之色,倒把王慶贊道:“啧啧,好拳腿!果是觔節!”那邊輸錢吃打的,與那放囊搶錢的兩個漢子,分開衆人,一齊上前喝道:“驢牛射的狗弟子孩兒,恁般膽大!怎敢跌我妹子?”王慶喝罵道:“輸敗腌臜村烏龜子,搶了俺的錢,反出穢言!”搶上前,拽拳便打。
隻見一個人從人叢裡搶出來,橫身隔住了一雙半人,六個拳頭,口裡高叫道:“李大郎,不得無禮!段二哥,段五哥,也休要動手!都是一塊土上人,有話便好好地說!”王慶看時,卻是範全。三人真個住了手。範全連忙向那女子道:“三娘拜揖。”那女子也道了萬福,便問:“李大郎是院長親戚麼?”範全道:“是在下表弟。”那女子道:“出色的好拳腳!”
王慶對範全道:“叵耐那厮自己輸了錢,反教同夥兒搶去了。”範全笑道:“這個是二哥、五哥的買賣,你如何來鬧他?”那邊段二,段五四隻眼瞅着看妹子。那女子說道:“看範院長面皮,不必和他争鬧了。拏那錠銀子來!”段五見妹子勸他,又見妹子奢遮,“是我也是輸了,”隻得取出那錠原銀,遞與妹子三娘。那三娘把與範全道:“原銀在此,将了去!”說罷,便扯着段二段五,分開衆人去了。範全也扯了王慶,一徑回到草莊内。
範全埋怨王慶道:“俺為娘面上,擔着血海般膽,留哥哥在此;倘遇恩赦,再與哥哥營謀。你卻怎般沒坐性!那段二,段五,最刁潑的;那妹子段三娘,更是滲濑,人起他個綽号兒,喚他做‘大蟲窩’。良家子弟,不知被他誘紮了多少。他十五歲時,便嫁個老公;那老公果是坌蠢,不上一年,被他炙煿殺了。他恃了膂力,和段二,段五專一在外尋趁厮鬧,賺那惡心錢兒。鄰近村坊,那一處不怕他的?他們接這粉頭,專為勾引人來賭博。那一張桌子,不是他圈套裡?哥哥,你卻到那裡惹是招非!倘或露出馬腳來,你吾這場禍害,卻是不小。”王慶被範全說得頓口無言。範全起身對王慶道:“我要州裡去當直,明日再來看你。”
段家堡大婚
不說範全進房州城去,且說當日王慶,天晚歇息,一宿無話。次日,梳洗方畢,隻見莊客報道:“段太公來看大郎。”王慶隻得到外面迎接,卻是皺面銀須一個老叟。叙禮罷,分賓主坐定。段太公将王慶從頭上直看至腳下,口裡說道:“果是魁偉!”便問王慶那裡人氏?因何到此?範院長是足下甚麼親戚?曾娶妻也不?王慶聽他問的跷蹊,便捏一派假話,支吾說道:“在下西京人氏,父母雙亡,妻子也死過了,與範節級是中表兄弟。
因舊年範節級有公幹到西京,見在下獨自一身,沒人照顧,特接在下到此。在下頗知些拳棒,待後觑個方便,就在本州島讨個出身。”段太公聽罷大喜,便問了王慶的年庚八字,辭别去了。又過多樣時,王慶正在疑慮,又有一個人推扉進來,問道:“範院長可在麼?這位就是李大郎麼?”二人都面面厮觑,錯愕相顧,都想道:“曾會過來。”叙禮才罷,正欲動問,恰好範全也到。三人坐定;範全道:“李先生為何到此?”王慶聽了這句,猛可的想着道:“他是賣卦的李助。”那李助也想起來道:“他是東京人,姓王,曾與我問蔔。”
李助對範全道:“院長,小子一向不曾來親近得。敢問有個令親李大郎麼?”範全指王慶道:“隻這個便是我兄弟李大郎。”王慶接過口來道:“在下本姓是李:那個王,是外公姓。”李助拍手笑道:“小子好記分。我說是姓王,曾在東京開封府前相會來。”王慶見他說出備細,低頭不語。李助對王慶道:“自從别後,回到荊南,遇異人,授以劍術,及看子平的妙訣,因此叫小子做‘金劍先生’。近日在房州,聞此處熱鬧,特到此趕節做生理。段氏兄弟,知小子有劍術,要小子教導他擊刺,所以留小子在家。适才段太公回來,把貴造與小子推算,那裡有這樣好八字?日後貴不可言。目下紅鸾照臨,應有喜慶之事。段三娘與段太公大喜,欲招贅大郎為婿。小子乘着吉日,特到此為月老。三娘的八字,十分旺夫。
适才曾合過來:銅盆鐵帚,正是一對兒夫妻。作成小子吃杯喜酒!”範全聽了這一席話,沈吟了一回,心下思想道:“那段氏刁頑,如或不允這頭親事,設或有個破綻,為害不淺。隻得将機就機罷!”便對李助道:“原來如此!承段太公,三娘美意。隻是這個兄弟麤蠢,怎好做嬌客?”李助道:“阿也!院長不必太謙了。那邊三娘,不住口的稱贊大郎哩!”範全道:“如此極妙的了!在下便可替他主婚。”身邊取出五兩重的一錠銀,送與李助道:“村莊沒甚東西相待,這些薄意,準個茶果,事成另當重謝。”李助道:“這怎麼使得!”
範全道:“惶恐,惶恐!隻有一句話:先生不必說他有兩姓,凡事都望周全。”李助是個星蔔家,得了銀子,千恩萬謝的辭了範全,王慶,來到段家莊回複,那裡管甚麼一姓兩姓,好人歹人,一味撮合山,騙酒食,賺銅錢。更兼段三娘自己看中意了對頭兒,平日一家都怕他的,雖是段太公,也不敢拗他,所以這件事一說就成。
李助兩邊往來說合,指望多說些聘金,月老方才旺相。範全恐怕行聘播揚惹事,講過兩家一概都省。那段太公是做家的,更是喜歡,一徑擇日成親。擇了本月二十二日,宰羊殺豬,網魚捕蛙,隻辦得大碗酒,大盤肉,請些男親女戚吃喜酒,其笙箫鼓吹,洞房花燭,一概都省。範全替王慶做了一身新衣服,送到段家莊上。
範全因官府有事,先辭别去了。王慶與段三娘交拜合卺等項,也是草草完事。段太公擺酒在草堂上,同二十餘個親戚,及自家兒子,新女婿,與媒人李助,在草堂吃了一日酒,至暮方散。衆親戚路近的,都辭謝去了;留下路遠走不叠的,乃是姑丈方翰夫婦,表弟丘翔老小,段二的舅子施俊男女。三個男人在外邊東廂歇息;那三個女眷,通是不老成的,搬些酒食與王慶,段三娘暖房,嘻嘻哈哈,又喝了一回酒,方才收拾歇息。當有丫頭老媽,到新房中鋪床叠被,請新官人和姐姐安置,丫頭從外面拽上了房門,自各知趣去了。
段三娘從小出頭露面,況是過來人,慣家兒也不害甚麼羞恥,一徑卸钗镮,脫衫子。王慶是個浮子弟,他自從吃官司後,也寡了十數個月。段三娘雖粗眉大眼,不比嬌秀牛氏妖娆窈窕,隻見他在燈前,敞出胸膛,解下紅主腰兒,露出白淨淨肉奶奶乳兒,不覺淫心蕩漾便來摟那婦人。段三娘把王慶一掌打個耳刮子道:“莫要歪纏,恁般要緊!”兩個摟抱上床,鑽入被窩裡,共枕歡娛。正是:一個是失節村姑,一個是行兇軍犯。臉皮都是三尺厚,腳闆一般十寸長。這個認真氣喘聲嘶,卻似牛齁柳;那個假做言嬌語澀,渾如莺啭花間。不穿羅襪,肩膊上露兩隻亦腳;倒溜金钗,枕頭邊堆一朵鳥雲。未解誓海盟山,也搏弄得千般旖旎;并無羞雲怯雨,亦揉萬種妖娆。
當夜新房外,又有嘴也笑得歪的一樁事兒。那方翰,丘翔,施俊的老婆通是少年,都吃得臉兒紅紅地,且不去睡,扯了段二段五的兩個老婆,悄地到新房外,隔闆側耳竊聽;房中聲息,被他每件件都聽得仔細。那王慶是個浮浪子,頗知房中術,他見老婆來得,竭力奉承。外面這夥婦人,聽到濃深處,不覺羅裈兒也濕透了。
事情敗露
衆婦人正在那裡嘲笑打诨,你綽我捏,隻見段二搶進來大叫道:“怎麼好!怎麼好!你每也不知利害,兀是在此笑耍!”衆婦人都捏了兩把汗,卻沒理會處。段二又喊道:“妹子,三娘,快起來!你床上招了個禍胎也!”段三娘正在得意處,反嗔怪段二,便在床上答道:“夜晚間有甚事,恁般大驚小怪?”段二又喊道:“火燎鳥毛了!你每兀是不知死活!”王慶心中本是有事的人,教老婆穿衣服,一同出房來問,衆婦人都跑散了。王慶方出房門,被段二一手扯住,來到前面草堂上,卻是範全在那裡叫苦叫屈,如熱鏊上螞蟻,沒走一頭處,随後段太公,段五,段三娘都到。卻是新安縣龔家村東的黃達,調治好了打傷的病,被他訪知王慶蹤迹實落處,昨晚到房州報知州尹。
州尹張顧行,押了公文,便差都頭,領着土兵,來捉兇人王慶,及窩藏人犯範全并段氏人衆。範全因與本州島當案薛孔目交好,密地裡先透了個消息。範全棄了老小,一溜煙走來這裡,頃刻便有官兵來也!衆人個個都要吃官司哩!衆人跌腳搥胸,好似掀翻了抱雞窠,弄出許多慌來,卻去罵王慶,羞三娘。正在鬧吵,隻見草堂外東廂裡走出算命的‘金劍先生’李助,上前說道:“列位若要免禍,須聽小子一言!”衆人一齊上前擁着來問。李助道:“事己如此,三十六餘策,走為上策!”衆人道:“走到那裡去?”李助道:“隻這裡西去二十裡外,有座房山。”衆人道:“那裡是強人出沒去處。”李助笑道:“列位恁般呆!你每如今還想要做好人?”衆人道:“卻是怎麼?”李助道:“房山寨主廖立,與小子頗是相識。
他手下有五六百名喽啰,官兵不能收捕。事不宜遲,快收拾細軟等物,都到那裡入夥,方避得大禍。”方翰等六個男女,恐怕日後捉親屬連累,又被王慶,段三娘十分撺綴,衆人無可如何,隻得都上了這條路。把莊裡有的沒的細軟等物,即便收拾,盡教打叠起了;一壁點起三四十個火把。王慶,段三娘,段二,段五,方翰,丘翔,施俊,李助,範全九個人,都結束齊整,各人跨了腰刀,鎗架上拏了樸刀,喚集莊客,願去的共是四十餘個,俱拽紮拴縛停當。王慶,李助,範全當頭,方翰,丘翔,施俊保護女子在中。幸得那五個女子,都是鋤頭般的腳,卻與男子一般的會走。
段三娘、段二、段五在後,把莊上前後都放把火,發聲喊,衆人都執器械,一哄望西而走。鄰舍及近村人家,平日畏段家人物如虎,今日見他每明火執仗,又不知他每備細,都閉着門,那裡有一個敢來攔當。
王慶等方行得四五裡,早遇着都頭土兵,同了黃達,跟同來捉人。都頭上前,早被王慶手起刀落,把一個斬為兩段。李助,段三娘等,一擁上前,殺散土兵,黃達也被王慶殺了。
奪取房山
王慶等一行人來到房山寨下,己是五更時分。李助計議,欲先自上山,訴求廖立,方好領衆人上山入夥。寨内巡視的小喽啰,見山下火把亂明,即去報知寨主。那廖立疑是官兵,他平日欺慣了官兵沒用,連忙起身,披挂綽鎗,開了栅寨,點起小喽啰,下山拒敵。王慶見山上火起,又有許多人下來,先做準備。當下廖立直到山下,看見許多男女,料道不是官兵。廖立挺鎗喝道:“你這夥鳥男女,如何來驚動我山寨,在太歲頭上動土?”李助上前躬身道:“大王,是劣弟李助。”随即把王慶犯罪,及殺管營,殺官兵的事,略述一遍。
廖立聽李助說得王慶恁般了得,更有段家兄弟幫助,“我隻一身,恐日後受他每氣。”翻着臉對李助道:“我這個小去處,卻容不得你每。”王慶聽了這句,心下思想:“山寨中隻有這個主兒,先除了此人,小喽啰何足為慮?”便挺樸刀,直搶廖立。那廖立大怒,撚鎗來迎。
段三娘恐王慶有失,挺樸刀來相助。王慶,段三娘與廖立鬥不過六七合,廖立被王慶觑個破綻,一樸刀搠翻,段三娘趕上,複一刀結果了性命。廖立做了半世強人,到此一場春夢!王慶提樸刀喝道:“如有不願順者,廖立為樣!”衆喽啰見殺了廖立,誰敢抗拒?都投戈拜服。王慶領衆上山,來到寨中,此時已是東方發白。那山四面,都是生成的石室,如房屋一般,因此叫做房山,屬房州管下。當日王慶安頓了各人老小,計點喽啰,盤查寨中糧草,金銀,珍寶,錦帛,布疋等項,殺牛宰馬,大賞喽啰,置酒與衆人賀慶。衆人遂推王慶為寨主。一面打造軍器,一面訓練喽啰,準備迎敵官兵。
起兵建國
且說當夜房州差來擒捉王慶的一行都頭土兵人役,被王慶等殺散,有逃奔得脫的,回州報知州尹張顧行說:“王慶等預先知覺,拒敵官兵,都頭及報人黃達,都被殺害;那夥兇人,投奔西去。”張顧行大驚,次早計點士兵,殺死三十餘名,傷者四十餘人。張顧行即日與本州鎮守軍官計議,添差捕盜官軍及營兵,前去追捕。因強人兇狠,官兵又損折了若幹。房山寨喽羅日衆,王慶等下山來打家劫舍。張顧行見賊勢猖獗,一面行下文書,仰屬縣知會守禦本境,撥兵前來,協力收捕;一面再與本州守禦兵馬都監胡有為計議捕。胡有為整點營中軍兵,擇日起兵前去捕。
兩營軍忽然鼓噪起來,卻是為兩個月無錢米關給,今日扁着肚皮,如何去殺賊?張顧行聞變,隻得先将一個月錢米給散。隻因這番給散,越激怒了軍士,卻是為何?當事的,平日不将軍士撫恤節制;直到鼓噪,方給發請受,已是驕縱了軍心。更有一樁可笑處:今日有事,那扣頭常例,又與平日一般猺剝。他每平日受的猺剝氣多了,今日一總發出來。軍情洶洶,一時發作,把那胡有為殺死。張顧行見勢頭不好,隻護着印信,預先躲避。城中無主,又有本處無賴,附和了叛軍,遂将良民焚劫。那強賊王慶,見城中變起,乘勢領衆多喽羅來打房州。那些叛軍及烏合奸徒,反随順了強人。因此王慶得志,遂被那占據了房州為巢穴。那張顧行到底躲避不脫,也被殺害。
王慶劫擄房州倉庫錢糧,遣李助,段二,段五,分頭于房山寨及各處,立豎招軍旗号,買馬招軍,積草屯糧,遠近村鎮,都被劫掠。那些遊手無賴,及惡逆犯罪的人,紛紛歸附。那時龔端,龔正,向被黃達讦告,家産蕩盡,聞王慶招軍,也來入了夥。鄰近州縣,隻好保守城池,誰人敢将軍馬捕?被強人兩月之内,便集聚了二萬餘人,打破鄰近上津縣,竹山縣,鄖鄉縣三個城池。鄰近州縣,申報朝廷,朝廷命就彼處發兵捕。宋朝官兵,多因糧饷不足,兵失操練,兵不畏将,将不知兵。
一聞賊警,先是聲張得十分兇猛,使士卒寒心,百姓喪膽;及至臨陣對敵,将軍怯懦,軍士餒弱。怎禁得王慶等賊衆,都是拚着性命殺來,官軍無不披靡。因此,被王慶越弄得大了,又打破了南豐府。到後東京調來将士,非賄蔡京,童貫,即賂楊戬,高俅,他每得了賄賂,那管甚麼庸懦。那将士費了本錢,弄得權柄上手,恣意猺剝軍糧,殺良冒功,縱兵擄掠,騷擾地方,反将赤子迫逼從賊。自此賊勢漸大,縱兵南下。
李助獻計,因他是荊南人,仍扮做星相入城,密糾惡少奸棍,裡應外合,襲破荊南城池。遂拜李助為軍師,自稱“楚王”。遂有江洋大盜,山寨強人,都來附和。三四年間,占據了宋朝六座軍州。王慶遂于南豐城中,建造寶殿,内苑,宮阙,僭号改元;也學宋朝,僞設文武職台,省院官僚,内相外将。封李助為軍師都丞相,方翰為樞密,段二為護國統軍大将,段五為輔國統軍都督,範全為殿帥,龔端為宣撫使,龔正為轉運使,專管支納出入,考算錢糧,丘翔為禦營使;僞立段氏為妃。自宣和元年作亂以來,至宣和五年春,那時宋江等正在河北征讨田虎,于壺關相拒之日,那邊淮西王慶又打破了雲安軍及宛州,一總被他占了八座軍州。那八座乃是:
南豐荊南山南雲安
安德東川宛州西京
那八處所屬州縣,共八十六處。王慶又于雲安建造行宮,令施俊為留守官,鎮守雲安軍。
渡江被捉
那時王慶手下親幸跟随的,都是假登東,詐撒溺,又散去了六七十人。王慶帶領三十餘騎,走至晚,到得雲安屬下開州地方,有一派江水阻路。這個江叫做清江,其源出自達州萬頃池:江水最是澄清,所以叫做清江。當下王慶道:“怎得個船隻渡過去?”後面一個近侍指道:“大王,兀那南涯疏蘆落處,有一簇漁船。”王慶看了,同衆人走到江邊。此時是孟冬時候,天氣晴和,隻見數十隻漁船,捕魚的捕魚,曬網的曬網。其中有幾隻船,放于中流,猜拳豁指頭,大碗價酒。王慶歎口氣道:“這男女每恁般快樂!我今日反不如他了!這些都是我子民,卻不知寡人這般困乏。”近侍高叫道:“兀那漁人。撐攏幾隻船來,渡俺們過了江,多與你渡錢。”
隻見兩個漁人放下酒碗,搖着一隻小漁艇,咿咿啞啞搖近岸來。船頭上漁人,向船傍拿根竹篙撐船攏岸,定睛把王慶從頭上直看至腳下,便道:“快活,又有酒東西了。上船上船!”近侍扶王慶下馬。王慶看那漁人,身材長大,濃眉毛,大眼睛,紅臉皮,鐵絲般髭須,銅鐘般聲音。
那漁人一手執着竹篙,一手扶王慶上船,便把篙望岸上隻一點,那船早離岸丈餘。那些随從賊人,在岸上忙亂起來,齊聲叫道:“快撐攏船來!咱每也要過江的。”那漁人睜眼喝道:“來了!忙到那裡去?”便放下竹篙,将王慶劈胸扭住,雙手向下一按,撲通的按倒在闆上。王慶待要掙紮,那船上搖橹的,放了橹,跳過來一齊擒住。那邊曬網船上人,見捉了王慶,都跳上岸,一擁上前,把那三十餘個随從賊人,一個個都擒住。
原來這撐船的,是“混江龍”李俊,那搖橹的,便是“出洞蛟”童威,那些漁人,多是水軍。李俊奉宋先鋒将令,統駕水軍船隻,來敵賊人水軍。李俊等與賊人水軍大戰于瞿塘峽,殺其主帥水軍都督聞人世崇,擒其副将胡俊,賊兵大敗。李俊見胡俊狀貌不凡,遂義釋胡俊;胡俊感恩,同李俊賺開雲安水門,奪了城池,殺死僞留守施俊等。“混江龍”李俊,料着賊與大兵殺,若敗潰下來,必要奔投巢穴。因此,教張橫,張順鎮守城池,自己與童威,童猛,帶領水軍,扮做漁船,在此巡探;又教阮氏三雄,也扮做漁家,守投去滟潤堆,岷江,魚複浦各路埋伏哨探。
适李俊望見王慶一騎當先,後面又許多人簇擁着,料賊中頭目,卻不知正是元兇。當下李俊審問從人,知是王慶,拍手大笑,綁縛到雲安城中。一面差人喚回三阮同二張守城,李俊同降将胡俊,将王慶等一行人,解送到宋先鋒軍前來。于路探聽得宋江已破南豐,李俊等一迳進城,将王慶解到帥府。宋江因衆将捕緝王慶不着,正在納悶,聞報不勝之喜。
淩遲處死
當日法司奉旨會官,寫了犯由牌,打開囚車,取出王慶,判了“剮”字,擁到市曹。看的人壓肩疊背,也有唾罵的,也有嗟歎的。那王慶的父王砉及前妻丈人等諸親眷屬,已于王慶初反時收捕,誅夷殆盡。今日隻有王慶一個,簇擁在刀劍林中。兩聲破鼓響,一棒碎鑼鳴,刀排白雪,纛展烏雲。劊子手叫起惡殺都來,恰好午時三刻,将王慶押到十字路頭,讀罷犯由,如法淩遲處死。看的人都道:此是惡人榜樣,到底骈首戕身。若非犯着十惡,如何受此極刑?
當下監斬官将王慶處決了當,枭首施行,不在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