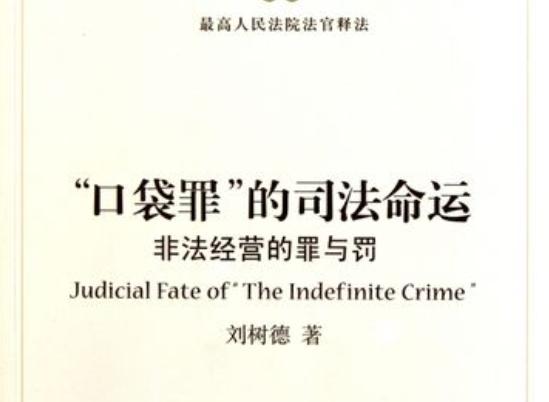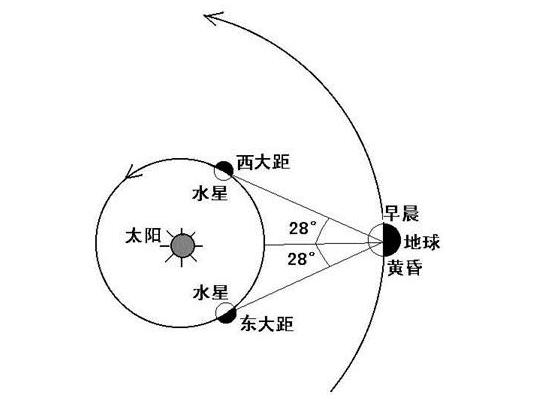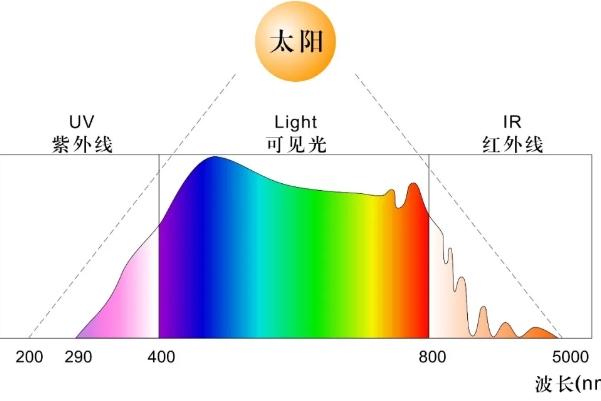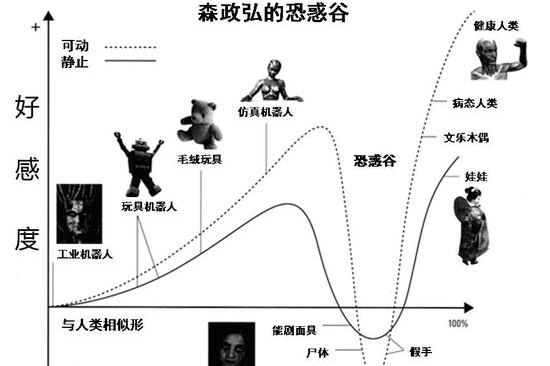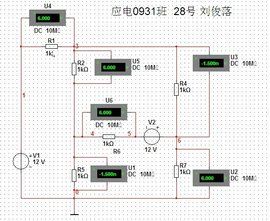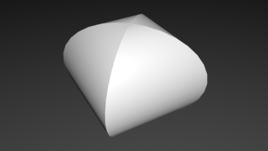权利
2002年底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草案,民法草案规定人的尊严和自由不受侵害,确立了人的一般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是针对如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具体人格权而言的。今后某些行为虽然没有侵害法律明确规定的具体人格权,但只要该行为最终损害了人的尊严或自由,就构成对一般人格权的侵犯,应受法律制裁。
可以说一般人格权规定是一种“口袋”式规定,能把除侵害具体人格权之外的侵害人的尊严或自由的各种行为囊括进来,从而给予惩罚。总而言之,规定一般人格权,就给人格利益以全方位的保护。
一般人格权,而且比喻也很生动——“口袋”。的确正如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在审议民法草案时所指出的,民法草案是一部公民权利宣言书。作为一个系统的权利规范体系,民法草案列举了可能列举的所有民事权利,以强化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但是在当今这个各种新型财产权和人格权不断涌现的“权利爆炸的时代”,单靠列举方法规定公民权利,难免挂一漏万,于是便出现了一般人格权这样的“口袋权”规定。有了这个“口袋”兜底,将更加有利于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充分尊重与保护。
立法形式
1、社会关系是纷繁复杂而又不断发展变化的,任何立法都很难穷尽社会现实,更难以预测将来,所以在立法时预留某种“口袋”以作兜底,是保持立法适应性和稳定性的现实需要。然而设置什么样的“口袋”,则大有讲究,反映着一国民主水平和法治状况。
2、“口袋罪”的价值取向,无疑是更好地维护法律秩序,即着眼于国家管理“公权”的有效实施,而不惜损害和牺牲公民个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口袋权”的价值取向,则在于更加全面、有效地维护公民私权利,保障公民个人自由,为此它可以限制甚至牺牲某种“公权”和社会利益。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体现了立法的不同时代背景。
3、改革开放之初通过的法律,更多的是着眼于国家运用法律这一利器来恢复和维持社会秩序,加之立法、司法水平不高,于是就出现了“口袋罪”并广为适用的情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开始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上层建筑,尤其是党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使得立法价值取向开始由国家和义务本位向着公民和权利本位转移,因而“口袋罪”的取消、“口袋权”的出现,就势成历史必然。
立法原则
1979年刑法的起草历经25年,共有35稿。1954年宪法通过后,第一届全国人大就决定制定刑法,当时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下属的法律室负责组织起草。1960年参与起草的,1963年出来了第33稿,但是不久就开始了“四清”、“文革”,起草工作被迫中断。一直到1978年宪法制定后,刑法起草工作才重新启动,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这些起草人员缺乏经验,不知道制定的这些条文实施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另外,当时正值社会变革时期,很多人存在害怕有立法疏漏造成打击犯罪不力的想法,主要考虑如何满足惩治犯罪的需要,而很少考虑副作用,因此起草条文时提出“宜粗不宜细”等原则。
采取对策
1、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废止了某些犯罪化的内容,如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不再笼统规定投机倒把罪,将部分内容合法化,其他需要规定为犯罪行为的尽量具体化;
2、分解,将流氓罪具体分解为寻衅滋事等四个罪名;
3、将民事、经济、行政法律中规定的各种“依照”、“比照”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文改为刑法的具体条款。
4、这些修改,其意是为了防止因立法的笼统性而导致实际执行中的随意性,使罪刑规定尽量明确化,体现了立法者意欲在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和人权保障功能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努力。
实践体现
玩忽职守罪主要是规定的内容相对较广,实践中并没有很大争议。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流氓罪、投机倒把罪和贪污罪。流氓罪主要是由于有“其他流氓活动”的规定,投机倒把罪则主要是因为对“投机倒把”没有作任何解释,而该词的含义又很不明确。
对“口袋罪”这个词进行评价,实际上就是对1979年刑法作一个评价。而评价这部刑法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考虑。当时,中国急需有一部刑法,首先这是治国安邦的需要,作为一个大国,在30年的时间里没有刑法,在国内出现随意捕人、杀人的现象,严重影响国际形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沉痛教训,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刑法的重要性、迫切性。总体上看,这是一部很成功的法律,当然,也存在原则性过强、不容易操作的问题,再加上执行中的扩大化,就造成了罪与非罪界限不清、互相混淆等问题,“口袋罪”就是其一。
“口袋罪”这一名词现在仍存在,有人就认为1979年刑法中的“大口袋”变成了现在1997年刑法中的“小口袋”,比如非法经营罪、寻衅滋事罪等。目前的刑法仍存在范围狭窄、操作难度大等问题,以后需要加强宽泛化、细化,尽量收紧这些“口袋”吧。
现状
在新刑法实施逾10年后,我们回顾一下就会发现,旧的“口袋罪”虽然消失了,但新的“口袋罪”又产生了;大的“口袋罪”虽然没有了,小的“口袋罪”却仍然存在。1997年新刑法颁行不久,取消投机倒把罪这个大“口袋罪”固然可喜,但留下一个“非法经营罪”这个小“口袋罪”却存在隐忧。
其他像寻衅滋事罪、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等也存在类似问题,如新刑法虽然将许多玩忽职守行为具体化为其他罪名,但仍然保留了“玩忽职守罪”这一罪名,这就造成不构成其他罪名的玩忽职守行为仍然可以纳入到这个“口袋”中来。其结果是,不但立法的本来目的(保障人权)没有达到,反而造成法典臃肿的弊端。
要真正实现良性刑事法治,立法只是第一步,观念的变革、执法机制和执法环境的改进等同样重要,与立法相比,后者甚至更需要生成的时间。同时,对立法上的改进,我们也不必过于简单地乐观,而要充分意识到社会时代特征对生活中的法律所产生的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罪刑法定”保障人权的要求,通过一种根深蒂固的法律精神和文化来优化法律的解释和运用,毕竟,法律再明确也是有局限的。如刑法中的“诽谤罪”在实践中产生出一定程度的“口袋罪”效应,但关于什么是“诽谤”,这恐怕不是立法所能明确的,更大程度上得靠司法来解决。
典型案例
明星因“流氓罪”获刑,“铁门啊铁窗啊铁锁链,手扶着铁窗我望外边”、“二尺八的牌子我脖子上挂呀,大街小巷把我游”《铁窗泪》、《愁啊愁》等多首以迟志强亲身经历为蓝本的“囚歌”,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这位“囚歌王子”1983年因跳贴面舞、与两位女性发生性关系以“流氓罪”被判刑四年。此前,他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青年演员。迟志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宣称“要撕掉罪犯的标签”,从而引发网友热议。
律师李炎辉在红网上发贴认为,从严格的法学角度来看,刑法中罪与非罪的规定,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社会形态中,统治力量平衡道德、经济等各种因素后诉求的集中表达,是一种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有学者评论说,从当年迟志强的“流氓罪”到今天陈冠希的“艳照门”,反思这几十年来国民在男女关系方面意识形态的变化是有意义的。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迟的‘流氓罪’是莫须有的,在今天至多是一些花边新闻,绝不会引起司法受到机关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