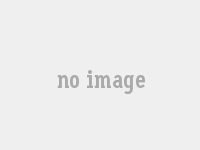社會主義
蘇聯、東歐等國所建立的社會主義是否是馬克思“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的具體實現?
理論界還流行着這樣一種觀點:馬克思不僅提出了落後國家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的思想,而且前蘇聯和東歐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已證明了馬克思這一理論的真理性。筆者認為,這完全是借助馬克思的隻言片語,斷章取義地對當代落後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注解。要回答當代落後國家的社會主義是否就是馬克思“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在現實中的實現,必須解決兩個問題。
首先,當代落後國家走上社會主義和馬克思的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有無必然聯系。縱觀馬克思緻查蘇利奇的四個複信草稿,我們不難發現,馬克思所醞釀的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思想是在非常嚴格的意義上使用的,應同時具備兩個條件。其一,農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存在,即:俄國農村公社“可以通過發展它的基礎即土地公有制和消滅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則來保存自己;它能夠成為現代社會所趨向的那種經濟制度的直接的出發點,不必自殺就可以獲得新的生命”。這就是“可以不通過卡夫丁峽谷”的前提和基礎。其二,資本主義現代化大生産的存在,即:俄國農村公社“和資本主義生産的同時存在為它提供了集體勞動的一切條件。它有可能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這是“可以不通過卡夫丁峽谷”的必要條件。就兩個條件而言,前一個更為重要,沒有土地公有制的先決條件,所謂的“不通過”也就無從談起。
俄國十月革命前是否具備這個先決條件呢?1895年恩格斯指出:“随着農民的解放,俄國進入了資本主義時代,從而也進入了公社土地所有制迅速解體的時代。”“俄國在短短的時間裡就奠定了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全部基礎”。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列甯也多次明确肯定俄國已經進入了資本主義時代。他指出:“民粹派往往根據我國國民經濟的技術落後和手工業生産占優勢等情況而把我國的制度和資本主義對立起來,毫無疑問,這是極端荒謬的。因為資本主義既存在于技術很不發達的情況下,也存在于技術高度發達的情況下。”由此可見,到十月革命前,俄國已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農村公社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的前提條件已經消失。所以,“跨越”的問題也就不複存在。
其次,蘇聯、東歐等落後國家所建立的社會主義是否是馬克思原意上的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在緻查蘇利奇的信中所醞釀的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直接進入的社會主義,必然是他曾作過多次描述的科學社會主義,而決不可能是遭到他多次批判的形形色色的其他社會主義。那麼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是否可以稱得上科學社會主義呢?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按照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所提出的“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原理,科學社會主義隻能建立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成就基礎之上,這是适用于人類社會發展的最一般的普遍規律。蘇聯和東歐等國在十月革命前雖已進入資本主義的低級生産階段,但自身卻缺乏發達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成果,所以,它完全不同于由發達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的情況。這種獨特的發展道路所産生的社會主義,是一種由于特殊的曆史條件所形成的、特殊曆史形态的社會主義。它和馬克思所說的由發達資本主義脫胎而來的社會主義形态,具有質的差别。這種質的差别歸根到底是由生産力的水平所決定的。因為不同的生産力水平決定着必然産生不同的生産關系和上層建築。從此意義上說,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不是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實現。蘇聯和東歐的這種特殊曆史形态的社會主義的出現,實際上是想走出一條不同于馬克思提出的由發達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的特殊道路。它的最終失敗不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破産。相反,它從反面驗證了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發展道路的學說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展示了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不可避免的曆史發展規律。
高巍翔:中國跨越“卡夫丁峽谷”的重大曆史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經濟文化落後國家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為核心的東方社會發展理論的成功範例,展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強大生命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體現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是“自然史的過程”與特殊條件下的跨越、生産力決定作用與生産關系能動作用和曆史活動主體選擇的曆史邏輯的統一。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改變了現代化的“單向趨同”,拓寬了民族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其理論體系正确回答了中國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後“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主題,在世界現代史上創造了“中國模式”或“中國道路”,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理論的内容,從而大大深化了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共産黨執政規律的認識。(《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學報》2009年第6期)
李方祥:西方國家争奪意識形态話語權呈現出三個新特點
一是在散布“意識形态終結”迷霧、“普世價值”神話的同時,把一般問題政治化、意識形态化,向其他國家輸出政治制度。貿易逆差、人民币彙率、能源、環境、軍費增長、人權等問題,是一些西方國家“妖魔化”中國的慣用武器。當今世界不同意識形态之間的對立和分歧仍然是客觀存在,敵對勢力攻擊社會主義國家為“極權主義政府”,始終沒有放棄對社會主義國家、對馬克思主義的敵視态度和立場。二是掌握和利用大衆傳媒對一些國家形成全方位、立體式包圍網。廣播、衛星電視等傳統媒體仍然是西方進行意識形态幹擾、滲透的重要途徑,而在近幾年來,更是加緊與我國争奪互聯網等思想文化的新陣地。三是利用國際經貿、文化交往不斷擴大的機會,在向一些國家輸入文化産品的同時,滲透美式自由、民主、人權等所謂“普世價值”觀。同時,利用各種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進行名為“文化交流”的滲透,使之成為輸出美國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渠道。西方敵對勢力的手法、花樣時常翻新,但反共、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立場是根深蒂固的,其戰略意圖和目标一以貫之。(《高校理論戰線》2010年第1期)
孔根紅:國外“中國觀察家”談中國共産黨的幾個核心觀點
在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下,一些國外“中國觀察家”将目光轉向中共并提出了幾個核心觀點:一是史無前例的“中國道路”。中共“沒有盲目照搬西方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譜寫了人類曆史上最重大的國家成就的篇章”,俄羅斯《紅星報》說,中共“提出了自己的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蘇聯由于沒有進行這樣的改革而解體”。奈斯比特、米歇爾·戈代等人認為,中共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現了時代的話題”,“正在改變全世界對中國共産黨的看法”。二是大智大勇的“變革創新”。奈斯比特說,“中國共産黨不再停留在《共産黨宣言》上”,“1978年,中國共産黨打開了與世隔絕幾十年的堅硬外殼,開始了神奇的蛻變”。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傅立民說,中共“奮發圖強、竭力趕超、自我反省、自我修正和适應變革的能力在過去28年中取得了驚人的進步”。庫恩說,中共有一種革新的毅力、前瞻的視野和寬廣的世界眼光,中國改革開放正是從中共政治觀念的變革與創新開始的,“他們厭倦了止步不前”。三是别具一格的“縱向民主”。“中國共産黨更加善于聆聽人民的意願”,順應民心“是中國共産黨經久不息的原因”。奈斯比特在新着《中國大趨勢》中将中國政治民主模式概括為“縱向民主”,獲得許多“中國觀察家”的贊同。他說“中國的縱向民主是建立在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上的”,“兩者的合力”促進了國家的強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當代世界》2009年第12期)
馬丁·雅克:不能再用西方模式解釋中國
過去30年,西方對中國的預測十有八九都是錯誤的,這已是一個闆上釘釘的事實。他們聲稱:中國經濟增長率被誇大;一場大危機迫在眉睫;國家的控制将逐漸減弱;全球媒體的影響将一步步削弱共産黨的權力。西方人預測中國之所以表現如此糟糕,是因為他們總是用西方模式和經驗來解釋中國。除非我們試着着眼于中國自身來認識它,否則對中國的看法将一錯再錯。中國截然不同于西方,做事方式或思維習慣迥異于我們。直面這個事實遠不如想象的那麼簡單。國家在中國人生活中仍無所不在,仍然擁有大多數大型企業,善于找到新辦法抵禦美國的全球媒體影響。西方觀察家通常認為中國政府的這種介入出于恐懼,但國家為什麼在中國社會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有更深層原因。在中國人看來,國家不是一種異己的存在,而是社會的化身和守護者。原因深藏于中國曆史。中國至少2000年前就已是一個文明國家。維護中國文明的完整被視為最重要的政治任務和國家的神聖使命,因而國家在中國具有與西方不可比拟的獨一無二的角色。(《環球時報》2010年1月18日)
王謹:确立中國問題意識,形成中國學派
現今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始終受制于西方範式。學術概念是西方的,研究方法是西方的,評價标準也是西方的,有的人已經到了唯西方馬首是瞻的地步,表面上提倡所謂“與國際接軌”,實際上是沒有辨别、沒有選擇地全面認同西方标準,進而全盤否定中國的學術研究方式和學術價值理念,全盤否定中國的學術研究、文化研究成果,丢失文化建設的主導權。還有一些同志對一些西方首先提出來的範疇和要領缺乏必要的批判性反思,滿足于人雲亦雲,或者趕潮流、求新奇,缺少在實踐中發展創新,甚至是把西方都早已摒棄了的東西奉若至寶,成為西方理論的附庸,導緻表面上新名詞、新概念層出不窮,實際意義卻不大,或者還會帶來負面影響。正是這樣的欠缺,成為“文化帝國主義”在全球化背景下對華實施文化“入侵”和“殖民”的一個危險“接口”。這種差距直接導緻知識界、學術界不僅始終無法站在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前沿,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理論範式,作出理論闡釋,提出發展思路,而且還在與西方的對話當中處于被動的境地,甚至于經常出現集體失語的現象。沒有中國問題意識,就不能建構出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社會主義文化。我們的學術研究、文化研究以及廣義的文化建設,都應當大力倡導中國意識,着力構建中國自己的社會科學理論創新體系和價值評判尺度。(《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9年第6期)
景天魁:發達國家福利的另一面就是貧窮、災禍
全球性金融危機更引起了人們對社會福利問題的深入思考和探讨。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但它卻是發達國家中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美國為了維持自己的高消費,還大舉借債。世界經濟秩序如此不合理,難怪美國華爾街的金融海嘯頃刻間就能席卷全球。正如研究金融危機不能就金融談金融、就經濟論經濟一樣,在社會學、社會福利和社會政策研究中,同樣不能就貧困談貧困、就福利論福利。福利國家的困境并不在于國内的财政困難,而在于越來越貧富懸殊的世界難以支持少數國家的高福利、高消費。所謂“福利國家”理論、“福利社會”理論、“福利資本主義理論”的最大局限是:隻以占世界人口零頭的少數富國為關照範圍和實踐基礎,它們的視野未能“普遍”到占世界人口大多數的不發達國家,甚至未能顧及到富裕國家内部的廣大貧困人口。那樣的“福利”其實另一面就是“失利”,就是貧困,就是災禍。“福利”這個概念的真正含義是普遍享有而非少數人獨享的利益。所以,讓人類真正邁向“普遍福利”的時代,是社會學、社會福利和社會政策研究的崇高目的和曆史使命。(《北京日報》2009年11月9日)
德國革命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緣起
馬克思出生于德國的特利爾城,那裡幾乎沒有工業,居民大多數是官員、商人和手工業者,他們主要經營葡萄果園為生。生于斯長于斯的馬克思十分關注本國社會的發展,對德國社會基本情況有深刻的認識。在《導言》中馬克思詳細分析了19世紀三四十年代德國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狀況。在經濟上,德國是一個生産落後的農業國家。國内封建割據的長期存在,嚴重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直到1834年德意志關稅同盟的建立,資本主義經濟才逐步發展起來。
“1837年蒸汽機由1826年的五十八台發展到三百二十八台,1844年棉織品和生鐵産量比1836年大約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但就全國來說,除萊茵河地區外,仍然是一個封建的農業國。”[2]馬克思認為,與英法兩國相比,德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十分緩慢,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巨大的落差。英法兩國在經濟較高發展階段暴露出的嚴重問題在德國尚未形成或僅處于萌芽狀态。“在法國和英國是要消滅已經發展到終極的壟斷;在德國卻要把壟斷發展到終極。那裡,正涉及解決問題;這裡,才涉及沖突。
在政治上,德國是一個封建專制的國家。1843年以前,德國沒有出現資産階級革命運動,雖然局部有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但國内封建勢力依然強大,國王威廉四世執掌國家大權。英法兩國工業革命和政治革命沒有導緻德國資産階級革命的爆發,馬克思反而認為德國封建專制統治由于其他國家資産階級革命反而暫時得到加強。“我們沒有同現代各國一起經曆革命,卻同它們一起經曆複辟。我們經曆了複辟,首先是因為其他國家敢于進行革命,其次是因為其他國家受到反革命的危害。”[3]3英法兩國的資産階級革命都經曆過多次封建複辟,才得以确立資産階級統治。
1640年英國爆發資産階級革命,後經數十年動蕩和王朝複辟,直到1688年的“光榮革命”才穩定下來;1789年法國大革命後發生幾次封建王朝複辟,一直到1848年2月法國二月革命才正式确立了資産階級的全面統治。馬克思認為,其他國家爆發資産階級革命而後又經曆封建複辟,這對德國封建統治者産生了雙重效應。第一,封建統治者發現其他國家由于爆發了資産階級革命,推翻了封建專制統治,因此害怕自己也遭受同樣的命運。
于是強化專制統治,壓制本國的資産階級,防範爆發資産階級革命;第二,封建統治者看到其他國家封建勢力的複辟,受到鼓舞,進而增強了維護封建專制的決心和信心。在這雙重因素影響下,國王威廉四世為了維護自己的封建統治,處心積慮,處處打扮成全社會利益的代表者進行欺騙。“這個國王想扮演王權的一切角色——封建的和官僚的,專制的和立憲的,獨裁的和民主的;他想,這樣做如果不是以人民的名義,便以他本人的名義,如果不是為了人民,便是為他自己本身。
馬克思指出,這種拙劣的欺騙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德國的政治生活中充斥各種弊端和醜惡,政治統治必然走向更加黑暗和腐朽。“在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可以看到一切國家形式的罪惡。
在文化上,德國是富有理論思維的民族。“德國人是一個哲學民族。”[4]在18和19世紀,德國先後湧現了像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格爾和費爾巴哈這樣偉大的思想家,在理論上産生了資産階級哲學——德國古典哲學,這是德國社會的獨特之處。“我們德國人在思想中、在哲學中經曆了自己的未來的曆史。我們是當代的哲學同時代人,而不是當代的曆史同時代人。
但是德國資本主義經濟十分落後,這種理論領域進步與經濟發展滞後的曆史錯位阻礙了德國的發展,帶來了嚴重的後果。“如果說德國隻是用抽象的思維活動伴随現代各國的發展,而沒有積極參加這種發展的實際鬥争,那麼從另一方面看,它分擔了這一發展的痛苦,而沒有分享這一發展的歡樂和局部的滿足。
也就是說德國資産階級在本國實踐中并沒有推行資産階級思想文化的優秀成果,推動德國社會的進步。德國當局反而強化了專制主義思想,文化上處于倒退的狀态,分擔了“發展的痛苦”。
總之,在德國社會,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毫無政治權利可言,完全處于被奴役的狀态。馬克思憤然指出:“這是一幅什麼景象呵!社會無止境地繼續分成各色人等,這些心胸狹窄、心地不良、粗魯平庸之輩處于互相對立的狀态,這些人正因為相互采取暧昧的猜疑的态度而被自己的統治者一律——雖然形式有所不同——視為特予恩準的存在物。”在英法兩國工人階級運動不斷高漲的曆史背景之下,作為革命家的馬克思,必然會深入思考德國革命将往何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