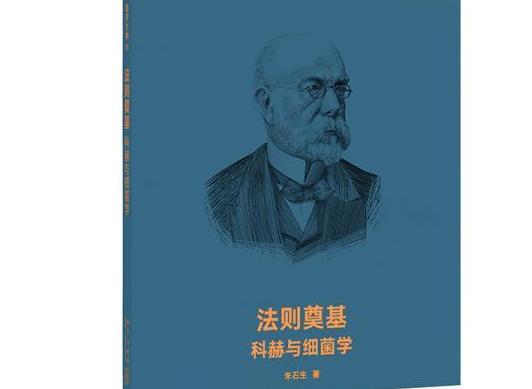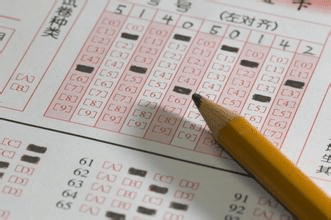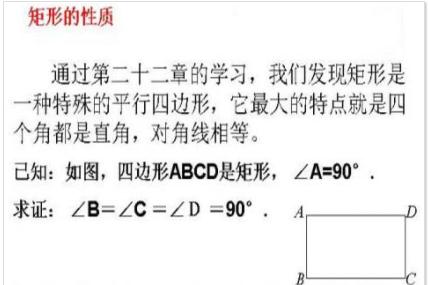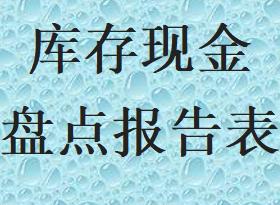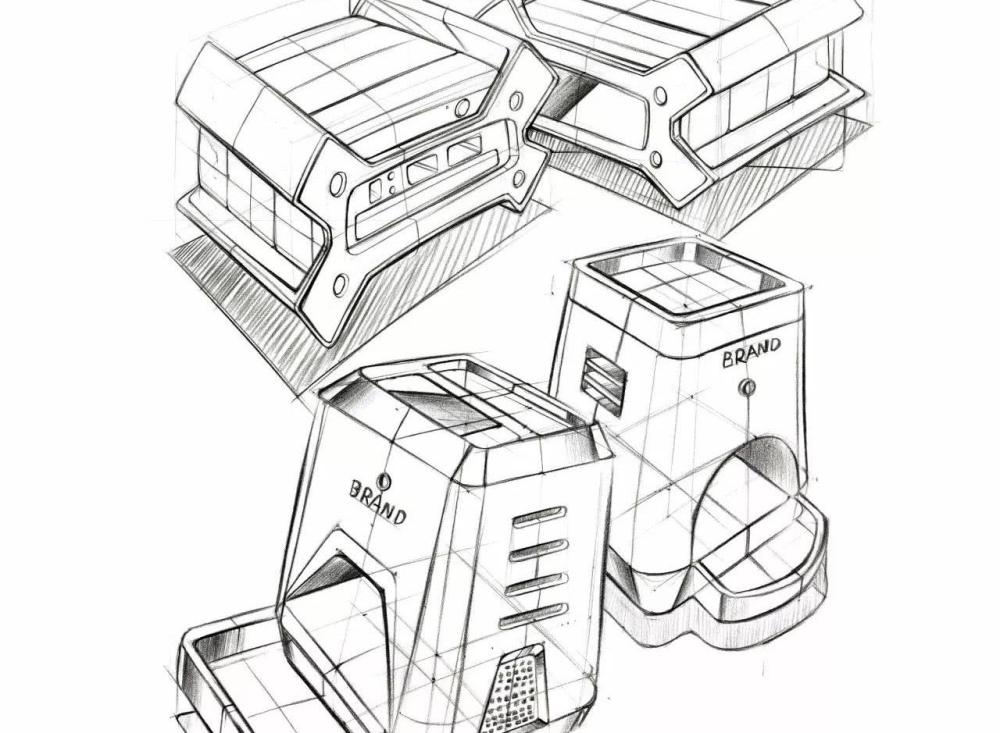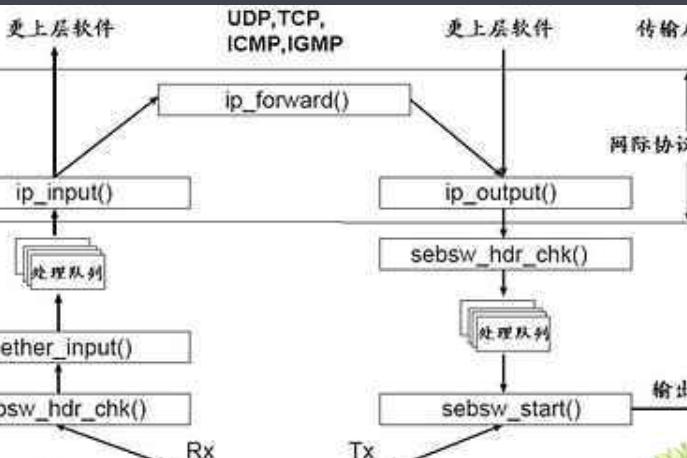基本概念
佛门讲“众生平等”。所谓“众生”,亦可理解为众人各自不同的人生。所谓“众生平等”,是说每个人在一生中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人生道路,无一不是依每个人自心本具的性德所生的结果。
佛家众生平等
来历
在佛陀的弟子当中,有不少人本来是外道门徒,后来经过佛法的薰陶,转而皈投佛陀座下,成为佛弟子。例如婆私吒、婆罗婆二人便是婆罗门出身的青年,当初他们跟随佛陀出家,引起其他婆罗门的责难,骂詈他们道:“婆罗门是至高无上的种族,是从创造宇宙之神的梵天嘴巴中生出来的,是梵天的继承人,而你们竟然与卑贱阶级的人民在一起,甚至礼拜这种人为师,简直是自贬身价!“佛陀听了,对弟子们说:“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方便而这样说罢了。他们说婆罗门是由梵天的嘴巴生出来的,那么婆罗门的女性就不由母胎生子吗?不管那一个阶级的人,都有做善事和做恶事的人,任何阶级的百姓,只要能够谨言慎行,身口意三业清净,舍弃一切执迷,努力开展自己的智慧,自利利人,这样的人便有资格被称为至高无上的人。”
佛陀这种众生平等的思想,引起各阶级人民的共识,纷纷加入僧团,打破印度四种姓的不平等制度。
众生依据其生存状态分为两种:有情众生与无情众生。凡是有情识的,如人与动物等,都叫有情众生,没有情识的,如植物乃至宇宙山河大地,都归为无情众生。
生态伦理意义
事实上,佛教的”众生平等“观念作为一种宗教理念和信仰的基础,对佛教信众的生活方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或许这些佛教信众并没有生态伦理的意识,或许他们并不了解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之间的相互关系,但他们严格按照佛教的清规戒律起居生活,在吃斋、放生和遵守不杀生戒律的过程中,赋予了在现代社会的文明人看来毫无生命迹象的植物、土地以佛性的尊重、呵护。把万物与人类相提并论,共同礼遇,甚至给予它们的敬重胜于自己的同类,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持生态平衡和保护自然环境的作用。
在古希腊时期,人们也曾经用一种敬仰或关注的目光去看待自然,把它看作具有灵魂的活的有机体。但在自然目的论观点的影响下,人们更多的时间是把人类放置在自然的中心位置。所谓的自然目的论认为,自然界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合目的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认为,在动物的繁殖与生成过程中自然给予了周密的安排和照顾。而经过驯养或者野生的动物可以作为人类的食物,其皮毛可以提供给人类制作成“服履”,其骨角为人类的工具提供来源。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就为动物生长着丰美的植物,为众人繁育许多动物,以分别供应他们的生计。”换句话说,自然界生长的植物是为了喂养动物,动物的存在是为了向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因而,自然在人们的眼里仅仅是人类生活必需品的仓库。可以说,人类中心主义的这种观念在人们的意识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成为人们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和评判万物的尺度。
基督教则从宗教的角度支撑着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即把人类描绘成上帝最钟爱的生命状态,甚至把他的形象赋予了人类,并告诫人类:“你们要生养许多儿女,使你们的后代遍满全世界,控制当地。我要你们管理鱼类、鸟类和所有的动物。”因此,基督教宣布说,上帝创造人类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并赋予人类管理和控制大地的权力。所以,怀特认为西方的“犹太一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构成了我们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并长期“指导着我们的科学和技术”,鼓励我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因此“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在于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如果说目的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提供的仅仅是一种观念和意识——一种靠理性的思考就能获得的观念和依靠信仰支撑的对宗教教义的解释,那么,文艺复兴运动的到来,使得人类中心主义改造和控制自然的目标有了现实的技术保证。特别是哥白尼的天文观察结果为人们打开了崭新的视野:地球与其他天体的物质是相同的,并且受同样规律的支配。于是,自然界在人们眼中又有了新的意义——观察和实验的对象。
伽利略则进一步把自然送进了实验室,分解成简单的形式和可度量的对象,并使它们服从数学的规律。于是,自然在人们的眼中便被看作是没有活力的物质。在此基础上,英国的培根通过他的《新工具》向人们宣布,了解自然不应是目的本身,实践才是目的。也就是说,利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来干预自然,支配自然,征服自然,这才是人类最终的目的。“知识就是力量”便是培根这一观点的集中体现。在培根看来。正是因为人的理性具有对自然、对事物的本质进行调查研究的能力,因而人类是能够支配自然的。这种思想构成了近现代西方思维方式的主导特征。
应当承认,对“自然”的新认识,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纺织机、蒸汽机的出现加快了西方文明的步伐。但同时,在人类企图通过技术革命调整和控制自然的过程中,人们对于人类以外的生命物种和自然环境的漠视和践踏。导致了生态环境严重失衡,由此也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这也迫使人们对自身行为进行反思,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反思,并将这种反思扩展到社会伦理的领域。传统伦理的作用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以善与恶、正义与邪恶来评判与规范个人、社会团体和政府的行为。生态伦理则是主张把传统伦理的道德标准、行为规范进一步扩展到人之外的生命物种身上。或者说,人类必须尊重各种非人类生命物种的“生存权利”,并以对待人类行为的善恶标准和评判方式处理人类与自然(包括各种生命物种)的关系。在关注人类的生存的同时,也必须关注其他生命物种的生存,并与之和谐共存。因此,生态伦理学导致的不仅是伦理学而且是整个人类自古希腊开始的价值体系和基本观念的改变。正因为如此,从传统伦理到生态伦理的转变对于人类来说是痛苦而且艰难的过程。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人类为了生存,一直在与自然抗争。中国神话中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大禹治水等都表达了先民对自然的抗争精神和欲望,这种抗争无可厚非。然而,人类想要控制自然则是另一回事。当人类以征服者的心态藐视自然,借助技术的手段控制自然时,尤其是当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类拥有了“上天揽月”的能力时,如果没有自觉的约束力,现代技术运用的结果造成的将是毁灭性的生态灾难。罗素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忧虑这种控制自然观念所带来的后果。他在《西方哲学史》一书中指出:“科学技术不像宗教,它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它保证人类能够做出奇迹,但是并不告诉人该做出什么奇迹。在科学技术必然要造成的各个庞大组织中,居领导地位的那些人在某种限度内能够随心所欲左右科学技术的方向。权利欲于是得到空前未有的发泄出路。在科学技术的激发下产生的各种哲学向来是权能哲学,往往把人类以外的一切事物看成仅仅是有待加工的原材料。目的不再考究,只崇尚方法的巧妙。这又是一种病狂。”
1983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递交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科学和技术的,科学方面我们有知识,技术方面我们有工具”。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并不是生态系统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也不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的,科学技术本身对自然没有善恶的观念和功利的追求,它听命于发现和制造它们的人类。今天的生态灾难是人类无节制的贪欲和企图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行为造成的。人类的行为则来源于他们根深蒂固的理念。它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极大的影响。并引导人们的一系列行为。所以“我们需要新的社会、道德、科学和生活概念。这些概念应由今世和后代人新的生活条件所决定。”生态伦理便是人类在面对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结果。
早在2000多年前,佛教就已经开始以一种谦卑和平常的心态对待一切生命现象,并在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进行着某些实践探索。而且其中的观点和理论经过了高度的抽象和思辨,并进行了严格的逻辑论证和本体论意义的探讨。有关“众生”概念的含义、“众生平等”的思想,与今天人们努力探索的有关生态伦理思想有着十分相似的思维方式和终极目标。不过,这些思考和实践大都是在宗教的信仰中进行的。问题是,我们不可能因为环境保护的需要,强迫全世界的人们都去信仰佛教。而事实上,今天的许多青年人在自然科学、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对信仰的观念、神灵的概念越来越淡漠。特别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宗教教义和观点只要求信众们毫无保留地相信它,不要追问“为什么”。这在自然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对在科学的批判精神熏陶下成长的一代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在科学发展的今天,用宗教信仰的方式来保护生态环境尽管是一个祖传秘方,但不是一副万能的灵丹妙药。
今天自然科学的发展为人类揭示了大量的自然奥秘和发展规律,使得科学地探究和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可能,为生态伦理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持,也为环境保护提供了科学技术的保证。但是。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发展仅仅有观念、理论和一系列政府政策还不够,生态保护只有成为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传统才有可能稳固、持久。持续了2000多年的佛教给予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尤其值得探讨和借鉴的是,在佛教的信仰中,关于敬畏生命、善待万物的“众生平等”思想不只是一个观念、意识和理念,它同时也是一种社会伦理,一种人类的善恶标尺,更是佛教信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换言之,佛教的“众生平等”不只停留在思想、观念的层面,它对生命的尊重,对万物的关注是落实在佛教的修行实践过程中的,体现在吃斋、放生等具体的生活细节中,规范在不杀生的戒律中。正因为如此.佛教的思想理念和实践活动能够延续2000多年,直至今日。
思想深意
”众生平等“这句话也被很多人误解。世界上一切众生之间、男女之间、甚至每一个兄弟姐妹之间,何曾平等过?有人穷,有人富,有人高高在上,有人卑贱如蝼蚁。佛法中所谓的众生平等,是指众生法性平等,对众生的慈悲喜舍心平等,在因果规律面前,众生平等,而非说众生的际遇平等,祸福平等。众生的差别,站在因果这个大环境下,就可以理解了,而且来得自然,也能让人心服口服。众生的不平等,是因为大家从无始以来,造的善业、恶业不平等引起的。有人行善多,有人行善少,有人作恶多,有人作恶少。没有理由要求不论作恶行善,转世为人之后就要得到相同的待遇。实际上,佛弟子四种也是有地位等级的,比如优婆塞、优婆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居士)见到比丘、比丘尼就要行礼,但比丘、比丘尼不用对优婆塞、优婆夷行礼。比丘尼见到比丘要行礼等等。这并不是什么等级制度,而是境地差别,相当于晚辈向长辈行礼,后进向先进行礼一样。
中国佛教对“众生”内涵的发展
尽管佛教是印度的宗教,但它在传入中国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融合中逐步发展为中国的佛教。其中的佛性论代表了中国佛教的基本特征,它为佛教的“众生”观念注入了新的内容,即以佛性作为众生平等的理论依据,把人类对生命的关爱和平等的理念由“有情众生”进一步扩展到了“无情众生”,提出了“无情有性”的观点,通俗的说法就是认为不但一切有情众生,而且如草木瓦石等无情众生亦有佛性。从中国佛教的圆融观点来看,不仅人类能够成佛、有生命的众生能够成佛,而且,那些在人们眼里可以任人宰割、任意践踏的“无情众生”同样具有佛性。从逻辑的角度讲,既然佛佛平等,具有佛性的有情众生与无情众生也平等无碍。因此,在中国佛教的天台宗、三论宗以及禅宗的牛头宗那里,众生平等指的不只是印度佛教中的有情众生之间的平等,同时也包括有情众生与无情众生之间的平等。
十六国时期北凉的译经大师昙无谶翻译了《大般涅槃经》,佛经提出了“一切众生(包括一阐提)皆可成佛”的观点,认为:“以佛性等故,视众生无有差别。”这一思想被佛教僧众们广泛接受。不过《涅槃经》中的众生指的是有情众生。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中,尤其是在儒家的心性理论影响下,经过魏晋南北朝有关心性与佛性的大争论之后,佛教开始形成有关佛性论的系统观点和理论,在隋唐时期就以创宗的形式宣告中国佛教的形成。其中,三论宗的吉藏、天台宗的湛然等高僧从中国佛教特有的视角——”圆融“的角度开始探讨佛性论问题——无情众生的佛性问题。禅宗的牛头宗则进一步发展出“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的观点,把佛与黄花、翠竹平等看待,使众生平等的理念更为广泛和充实。
中国佛教的这种“圆融”思想,在吉藏那里被理解为”一切诸法依正不二“。“二”即是“异”、差别、对立、矛盾。不二,亦即无差异、无矛盾。《大乘义章》解释说:“言不二者,无异之谓也,即是经中一实义也。一实之理,妙理寂相,如如平等,亡于彼此,故云不二。” “如如”是真如之意,亡于彼此即无分别之意,实义则指宇宙万物的实相。因此,一切现象的真如、实相离(不是)一切差别相,而是超越二与不二的分别,一如无二、平等无二。吉藏在这种“如如平等,亡于彼此”的基础上推论出无情众生也有佛性的观点。吉藏论证说:“以依正不二故,众生有佛性,则草木有佛性。以是义故,不但众生有佛性,草木亦有佛性也。若悟诸法平等,不见依正二相故,理实无有成不成相,假言成佛。以此义故,若众生成佛时,一切草木亦得成佛。吉藏在这里明确地表明,一切众生都是处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因果关系中,离开无情众生,有情众生就不可能存在。因此,生命主体同生命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天台宗的“圆融”思想是通过智颤“一念三千”说体现出来的。“一念三千”是“一念心具三千世界”的略称。所谓“一念”在智颧那里指的是一念心、一心,即心的一念,是心念活动的最短时刻,用佛教的概念就是“一刹那”。那么“心”又是何物?智颇在《摩诃止观》指出“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法性也就是实相、真如。至于“三千”或“三千世界”,智额解释为:夫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具十法界、百法界。一界具三十种世间,百法界即具三千种世间。”
在智颇“一念三千”的基础上,湛然提出了“无情有性”的思想,即草木等无情众生与有情众生一样具有佛性。在他看来,既然佛性是众生的本性,也是万法的本性,那么,“言佛性者应具三身。不可独云有应身性。若具三身法身许遍何隔无情。二者从体三身相即无暂离时。既许法身遍一切处。报应未尝离于法身。况法身处二身常在。故知三身遍于诸法何独法身。法身若遍尚具三身何独法身。三约事理。从事则分情与无情。从理则无情非情别。是故情具无情亦然。”既然刹那一念具足三千世间,便是刹那一念心遍周法界,那么,佛性也具有三身,应身、法身和报身,不可能只具应身。由此,湛然的结论是:“是则一尘具足一切众生佛性。亦具十方诸佛佛性。”草木、瓦石同样不例外,与其他有情众生一样具有佛性。湛然从天台宗的圆融思想推导出无情众生有佛性的观点,把众生平等的思想贯彻到了无生命的物质世界。
禅宗的牛头宗则把老庄与魏晋玄学的“道”、“以无为本”的概念和思想引进了佛学,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提出了“道遍无情”的观点。这是湛然“无情有性”的另一个版本,当然,这个版本更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众所周知,“道”是老庄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尽管包含的意思很多,但第一的要义是本体论意义的,即指宇宙万物的基始,魏晋玄学在老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以无为本”的思想,试图用思辨的方法来探讨万物存在的根据。牛头禅的创始人法融在佛教“性空”的思想中添加了道家玄学的概念,提出了“虚空为道本”的命题,所谓“虚空”即是性空的别名。“道本”在法融那里也被解释为具有“离一切限量分别”的佛法之根本。他的原话是:“夫道者,若一人得之,道即不遍。若众人得之,道即有穷。若各各有之,道即有数。若总共有之,方便即空。若修行得之,造作非真。若本自有之,万行虚设。”所以,方立天指出:“就此命题的思维形式来说,显然是受到了魏晋玄学‘以无为本’说的启发,就此命题的思维内容来说,也是与‘以无为本’说相呼应的,然就此命题的思维实质来说,则是般若学与道学两种不同思想的折中、调和。”
如果说,天台宗的“一念三千”是以心性论为出发点、从境界的视角论证“无情有情”,那么,牛头宗则是以老庄的“道”,以玄学的命题形式,把道或者佛性或者法性置于超越心物之上的宇宙本体高度。既然佛性已经成为宇宙本体,既然佛性就是“道”,那么,“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观点也就完全合乎逻辑地被推论出来。因为,本体论意义上的“道”是没有有情与无情之分的。也正是牛头宗的玄学特色——从宇宙万物的本原出发,使得佛教“一切众生皆能成佛”的思想具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胸襟。对于今天的生态伦理来说,它更是提供了一种思考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思路和方法。